中国民间称“春节”为“过年” 我国现行“春节”今年104岁
关于过年、家乡和新衣服,我们有各自的故事要讲
在外界眼里,乡土以及过年,是和我们天天报道的奢侈品、时装完全不搭边的话题——至多了,是想看看热闹,比如什么平日里背着LV的Lucy坐着硬卧火车,回家换身棉袄变成虎妞之类的段子。
但就像我们曾在一篇稿子里说到的那样,时装的确是个肤浅的东西,肤浅到男女老少们以为换上件Prada的新品就等同重获新生,但它也深奥,深奥到几乎没人能拒绝它的肤浅。
都说要衣锦还乡,无论是城里人追捧的上万块的名牌,还是虎妞铁蛋的花棉袄,又或是你家乡的千万广厦,我家的平房砖瓦,终归是人们在物质中修炼人生的道具而已。所以我们也很庆幸,能够透过这肤浅的时装,寻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哲学。
所以到了春节,我们想,算了,回家了,也该歇一歇,听了那么多别人的事情,不如说说自己人的,底下就是时尚组编辑和记者各自在老家过年时,经历的、或者听到看到的关于衣服和人的故事。
《表姐》
文|钱沐炻
表姐是我姨的闺女,比我大五岁,其实不到动笔前,我都没正式叫过她姐,她也从来没叫过我弟弟,我俩甚至互相连小名都不喊,因为就算有机会,估计也不肯。
虽然户籍是天津,但我们都不敢说是这个城市的原住民。我呢,从小因为家庭的缘故,始终往返在北京和天津这两座城市,后来工作了一直在北京,期间也在上海待过一段,心里没那么强的乡土概念。
表姐就更复杂了,她母亲是天津人,父亲是宁波人——30多年前,我姨在上海做小生意时遇到了早就下海从商的姨夫,结婚没多久,生了表姐。我姨和姨夫吵架时总抱怨要是听老例儿就好了,嫁个外地人受欺负。我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直到看了《师傅》那部电影才明白过来,因为小宋佳演的女主角在戏里说过一句:“天津姑娘不外嫁”。

表姐10岁左右时才回天津念书,小时候我听大人聊天时说她在学校经常挨欺负,同学都叫她“南蛮子”甚至“洗头妹”,因为她的确不像是本地人。那时候城市人口流动性远不如现在,但凡人有一点不同,就会被视为异类,她的同学肯定是把她和当时流行的、同样是背负着南方印象的温州发廊妹混为一谈了。
她小脸小嘴、单眼皮,皮肤白,是标准的江南姑娘长相——更甭提她那一口吴语腔的普通话了,我姨曾经教过她说标准的北方普通话、甚至天津话,她学得荒腔走板,我姨为此总骂她笨。
我家族人不多,平日互相来往也少,也就是到了春节,能凑到一起。大人和小孩子各自聚成一团,我和表姐是两个不合群的怪胎,连轮到我俩分别给姥姥姥爷拜年时,周围的气氛都能瞬间降到冰点。
我俩总是各自绕着屋子转了一圈后,聚到姥姥家放杂物的小屋里。以前没暖气,炉子的热度又不过那屋,所以很冷,没人去——现在想想,纳了闷了,总共也没几个小孩儿,也没几间屋,为啥我俩就只能找那么个地儿待。
但就算待在一起,我俩也没什么话可讲,就听着旁屋的动静,看着屋里的杂物,我记得我会翻出几本过期的《上海服饰》看,表姐也凑过来看,我就是百无聊赖地翻页,表姐一句话不说,但我感觉有时候她其实想自己拿过去看,但她不说,她等着我说,可我也是不说。
我比表姐还是幸运点的,小时候过年,大人总会给孩子准备一套新衣服,我记得我妈还曾在北京的赛特商场给我买过一套蓝色抓绒运动衣,上面有个小熊,一按就叫。那衣服好像是花了800多块钱买的,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几乎成了当年春节轰动全家的新闻——谁叫我妈也爱打扮呢,她再不会像传统爹妈一样溺爱孩子,也总会按自己的方式表现,只可惜我当时还太小,觉不出穿新衣贵衣的好,就像个小狗不愿意挪窝一样——旧衣服穿着多好,闻着味道都亲切!
印象里,表姐没什么新衣服,总是穿一条黑棉裤、一双破旅游鞋和几件印着不同花色的灰毛衣,灰得跟我姨和姨夫的脸色一样。那两年他们生意做砸了,本来就拮据的经济状况更是一落千丈。
过了很多年,我妈告诉我表姐其实也想要新衣服,她总偷偷盯着我的衣服看,我妈想给她买,我姨坚持不要,所以那几件灰毛衣,其实是我妈织给表姐的,但我妈也是从小娇生惯养,手工活做得很一般。
可我妈还是想给表姐织几件好看的、亮色的毛衣,小姑娘嘛!但我姨就是不许,说她那么笨,学习成绩也不好,穿得花里胡哨做什么。我妈说那些年,我姨和姨夫把外面的气都撒到自己女儿身上了,这姑娘命苦,就是来还债的。
有一年春节,还是那么大人、那么多小孩,聚在姥姥家,我照例躲到了冰冷的小屋,《上海服饰》都翻了好几遍了,却迟迟不见表姐进来。
过了一会,我听到大人那屋传来了打骂声,跑过去看,我姨和姨夫正轮番打表姐,骂她大春节的丢人,什么都不行就知道瞎臭美——他们打得真凶啊,一巴掌一巴掌地往表姐身上抽。
但表姐就是侧着身子蹲着,用一只胳膊挡住自己的头,她快蹲不稳了,但一声不吭,一声不吭。
大人们似乎是过了有一阵子才反应过来,把我姨和姨夫劝走了。
表姐还是到小屋里来了,她那条黑棉裤的裤裆处明显比别的地方颜色都要深,她的嘴唇有点红,但比不上脸上的痕迹更红。她没哭也没说话,偶尔把毛衣袖子撸起来用手臂抹抹鼻子,我只记得那次我翻杂志的速度慢了很多。
后来也是我妈告诉我,表姐挨打是因为偷偷抹了舅妈的唇膏,还是她发现的,说挺好看,结果却让侄女糟了罪,她为这事内疚不少年。
后来谁也想不到,表姐念大学时和一个新加坡人好上了,没毕业就去了对方的国家结了婚,后来又辗转法国、澳大利亚。
过年时,总有亲戚问表姐现在情况如何,我姨和姨夫只说挺好的,结果自然有人传表姐不学好,傍大款,真够呛。
她就是这么一个人,没人知道她的出走或者沉默,是蓄谋已久的反抗,还是听天由命的偶然。表姐的人生,可以是一本流行小说的素材,但她偏偏不给写书的、或者看书的留下他们想要的线索。
结果我们再见时,我都没办法把她和当年的小姑娘联系到一起了。简单从外表说,她已经是灰姑娘穿上水晶鞋的阶段了。
亲戚们也认不出她,特别是在已经近乎民间名利场的春节团聚之时,表姐的穿着和神态不要说能在周边亲戚身上的貂皮大衣、Fendi手提包中脱颖而出了,即便放到最繁华的地段,也是数一数二的。他们称赞表姐国外这些年没白混,甚至要变着法地蹭光,我姨和姨夫还是不说话,他们就浅浅地笑。
“这包什么牌子的啊,真好看!”表姐笑了笑没作答,结果亲戚硬是抢去翻商标,问是不是Dior,但其实是Delvaux.
亲戚们唯一的不满,是表姐没穿“水晶鞋”,而是一双有些脏的Reebok球鞋,这自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表姐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衣锦还乡、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架势,她不是复仇来的,仍旧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微笑。
但我俩都没再躲到姥姥家的小屋里。直到亲戚走了一半,我俩才说上话,当她知道我做了时装媒体这一行,话才多了一些——她的普通话还是带着点吴语口音,但已经很淡很淡了。
表姐告诉我她当年走了之后,先是跟着丈夫学做餐饮店铺设计,后来又去念书改行做了平面设计,现在他俩在墨尔本有一家小餐厅。对了,之前在巴黎住的时候,她还认识了一些做时装行业的人,因为自己爱买,慢慢也爱研究这个行业,下回要向我请教。
表姐的穿衣并不需要向谁请教什么,后来过年再看到她,更加剧了我的好奇,她到底是如何练就这一身不显山不露水的调调的?
关于过去,我们从来没细聊过,但我相信她现在的一切,不是因为单纯身在海外、嫁了外籍老公或者读了什么杂志而来的。
可故事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美好,去年除夕,表姐没回来,结果过了元宵节才慌慌忙忙地连招呼都没打就飞了回来。听我妈说她丈夫出了什么事,究竟是有了外遇,还是出了意外,谁也不知道,她照旧不怎么说话,更没哭,只是裹了一件羊毛大衣、头发都没梳,穿着高跟鞋提个箱子就回来了,然后待了三天走了。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祝我春节好,此外再无他语。
今年年底,我姨和我妈逛街时,看到一件Celine的毛衣,她问我妈表姐穿会不会好看,想买给她,但还不知道表姐今年过年回不回家。
毛衣买回来了,我妈指着iPhone里的照片,说这是我姨买给表姐的,问我好不好看。
人长大了,总觉得过年没意思甚至是负担,什么故乡啦新衣服啦好吃的啦全都成了过去的回忆,但今年,我倒是盼望过年,盼望过年时能看到表姐,盼她一切都好。
《年夜衣文》
文|邵卉
至少有七、八年没为春节特意买过新衣服了。一来上海年味越来越淡,串门机会少;二来,我们现在买衣服很不太需要借新年由头,兴致一来就下单了。回想以前寒假开始后,由妈妈领着轧马路,先去百货商店打样,随后转战陕西路一带外贸店淘尖货——这套流程还怪叫人怀念的。
小时候,我总是和新衣服较劲,尤其到了重要场合,比方说新年做客。从隔壁建筑工地滚了满身黄沙回来算小事,一顿年菜吃下来总有几筷子会掉到身上,最后被迫像短手霸王龙那样,用目光示意长辈帮忙夹菜。即便最保险的黑色,轮到我身上也会出事,比如踢了一脚路边的塑胶桶,结果满满的白漆撒了出来。
等到长大了些,其实也就13、4岁,小姑娘知道臭美的时候,突然间信心爆棚,觉得自己能够驾驭白色。时至今日,我都没弄明白怎么会萌生这个想法,当时可没有全智贤白色滑雪服同款啊!总之入冬不久,我就在家软磨硬泡央求买新羽绒衣,而且非要全白。
当时的上海开出了不少外资百货,听说就连浦东(“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观念当时还挺盛行)也开了一家,名叫八佰伴,上海话含糊读来就跟“八八八”似的。绝大多数人不会乘坐过江隧道跑去浦东购物,要买新衣服还是会去南京路上那一串百货店,从西藏中路一路向东“检阅”每家店铺产品。惠罗几乎在南京东路的尽头,距离外滩不过两条马路,一到冬天就会办羽绒服博览会。
半大不小的孩子那时候买起衣服可不会在意品牌、质量,颜色和花纹胜过一切。惠罗羽绒那层开有几十家品牌,空气里飘着股菜场禽类区的味道。各家商铺都爱用龙门架做隔断,矮个子往往一扎进去就只好像迷宫一样兜兜转转。我甚至想过用声音做标记,因为那里铺着木地板,有些地方走过就会咯吱作响,结果可想而知。
至于最后在哪家成功找到就真的记不清了,只知道它是件薄薄的白色长款羽绒服,帽沿上有一圈细细软软的兔毛——孩子总擅长自行脑补。随后那些天,这件衣服在房间衣橱挂了好几天,等到真正上身已是大年初一去外婆家拜年的日子。
那天,我特意绕开鞭炮、水洼、垃圾桶、乱跑的熊孩子、疑似有些脏的公车座椅等高危障碍……一路左躲右藏终于平安抵达。新衣服的新鲜劲儿其实持续不了很久,走过一套拜年流程,听完一长段似懂非懂的攀谈后,我们好不容易等来午饭。根据往年经验和厨房探访,酱油蹄髈、松鼠黄鱼、八宝鸭、三鲜砂锅、春卷等年菜肯定一个不少——各个都是白色衣服的冤家。
显然我不能,也不愿意以身犯险穿着白色的新衣服上桌,但光穿里头的毛衣又有着凉风险。风度和温度这道选择题前,孩子基本没有自主权。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外婆的姨妈红棉袄和表妹的校服——就是那个年代上海初中生身上绿油油的长袖拉链衫,还配有两道黄色饰边。
记忆里,那顿饭我大概只坚持了半小时就跑开了。当然,现在过年的家族聚餐持续时间其实也不长,撑死了俩小时——也很少有人会为了这顿饭打扮得入时,反正我是经不起因为一件自己觉得好看的衣服,招来七姑八姨们的唇枪舌战。
家衣文/周卓然
今年春节,我不回家里陪爸妈过年,而是准备初一那天出门旅行。这是我第一次这样任性,但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因为父亲工作和我求学的关系,我从小到大住过好几个城市,每一个都至少三年,从南方到北方,从西部到东部,一个人久了,似乎对故乡的情感也愈加地淡漠。我对父亲说我错峰回家看他们,而他说一早就选择了放飞我,就没想过我会回去。
临近年三十的日子近了,也常能收到许多旧友的祝福信息,但就属那晚和小安聊得最多。小安也不回家,她在美国读书,学的是印花设计,这个时间正忙着创作和教课。我们都很高兴,一个华人女孩还没毕业就得到了给当地学生当老师的机会,真的很难得。
我和小安是三年前在美国费城偶然联系上的,在那之前是十几年的失联。那是一个秋日午后,我坐在竖着红色“Love”的雕塑喷泉前等她,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红色袍子的长发女孩,她的头发黑得和墨汁一样,显得衣服就更加红艳了。走进了看,那件袍子上绣着一堆我不认识的动植物,但廓型却很像一件苗衣。小安说,她专门穿了这件她最爱的衣服来见我。
这样的小安和我记忆中的她不同。我们11岁认识,那时同在四川一座以少数民族杂居、湖南、东北、广东移民为主的城市念书,因为前来支援三线建设的人口结构比较复杂,同一个国企和省份的人总是住在一起,久而久之,都知道了彼此的贫富差异。
来自东北的小安住在较为贫困的片区,那里已经是郊县,快要靠近云南。她的性格很要强,有时候甚至有些高傲,因为是满族人,一次一个同学说她的姓很少,小安答道:“那是因为放在过去我就是格格,是镶黄旗。”我依稀记得,她的英语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每个读音都会咬得特别准。
其实排除经济因素,小安的家是个难得的百草园,那里山上的花草鸟虫常常飞进民居,还总能见到国家保护的珍奇异兽。从小就爱爬树的她留着一头比男生还短的头发,经常穿一条背带裤,在比四层教学楼还高的树上爬来爬去,上课铃响了也不下来,还把树顶上的猫头鹰宝宝偷下来带回宿舍,最后把猫头鹰妈妈引来了。老师骂她,她就顶嘴,然后摔书走出大门。
但就算这样,小安的成绩还是能排进年级前几名。她很聪明,经常也不听讲,却把许多精神放在画画上。有几次我扭头看她,她都在画一些长着尖耳朵的精灵、长尾巴的男孩、榆树怪物之类的,笔法很自然,画面也很魔幻。
我时常惊异于她一天美术都没有学过这件事。高中学理科的她考去上海念了大学,学的是纺织机器,学校里选派优秀学生留学,她是其中一个。离开故土的她终于放开了自己的限制,她就这么拿着二十几年积累的野路子作品进了美国最难考的设计学院。这让我三年前站在她铺满画纸和立体作品的公寓里时,感动得差点哭出来。
这些天我们又在微信上聊起了这些事,我问她美国人到底看上了她什么,事实上当年我的一个清华美院学画十几年的朋友都没能进得了那所大学。小安回答说,她知道自己有天分,而且力量巨大。如果没有出生在那样草长莺飞的故乡,她应该无法发现老天给的这份礼物。接着,她传过来一张近照,蹲在草丛里的她捧着一堆不知名的果子笑得很开心。我想,这一点却和小时候的她很像,还是那么喜欢炫耀自己在植物学上的博闻广记。
我看到照片中的女孩还是穿着我们重逢时的那件红色袍子。小安说过,那是她几年前在上海买的,当时看到时就觉得触动,看多了奢侈品,竟然觉得民族风反而洋气了起来,红色、喜庆、特别、就算不是新的也适合过年,“在美国很有创造力,在上海也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每次当车子停在家门的那一刻,却总觉得失去了一切斗志,好像生活就这样平凡也很好。所以我越来越不敢回去了,我必须一直用力往前跑,我不是想要追光,也许只是害怕黑暗。”小安说。我回她说是的。
的确啊,在外乡才会顾念家乡的好,我们都知道,那些素年锦时早就刻进骨头里了。但是可惜,故乡,都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穿红》
文|楼婍沁
把购物选项勾选“红色”后,屏幕上一排排的红色上衣实在有点晃眼睛。但没办法,还是要睁大眼睛,快选快买。不然再过两天快递停了,过年去爷爷家吃饭就穿不上了——这可是我过年前的头等大事。
从我懂事起,每年过年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大年三十去爷爷家吃年夜饭。这天是一定要穿上新衣服的,最好还是红色。这是爷爷的规矩。就和他还要求每一年的年夜饭桌上一定要有炒藕片、红烧鱼一样。他总说吃了藕来年就能“路路通”,做盘鱼为的是家里能“年年有余”。至于穿红色新衣,他收藏的吉祥话更多,比如“开门红”、“新年新开始”、“红红火火一整年”……
不过,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守这个规矩了。
之前年纪半大不小的时候,我一直拒绝穿红戴绿,坚持穿黑、白、灰,最鲜艳的也就是穿藏青或者米黄。倒不是因为叛逆,只是有一种少年追求“酷”劲的执念,当时觉得那是穿红色没办法实现的。而年岁渐长,酷不酷变得没那么紧要了,不穿红色的新衣服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当然,爷爷并不喜欢我的这个习惯。往往是三十那天,我一走进他家门,他就会皱着眉头盯上我老半天;有时开饭前,还会走到我耳边嘀咕句“穿红色才好看”;等到了饭桌上,他就开始不停地给我夹藕啊、鱼啊,然后每夹一筷子,就要祭出吉祥话的大招。
我知道那是他想“抵消”我穿深色衣服带来的“杀伤力”。现在想来还觉得这样挺可爱的。但小时候难免有被念叨得不甚其烦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唯物主义”,“拒绝迷信”一类的说辞是我最常用的套话,可以用来和爷爷辩论好几个回合,争不出输赢。直到有一次我问他,“你不是也没穿新衣服吗?”,才发现原来他也是能被一招制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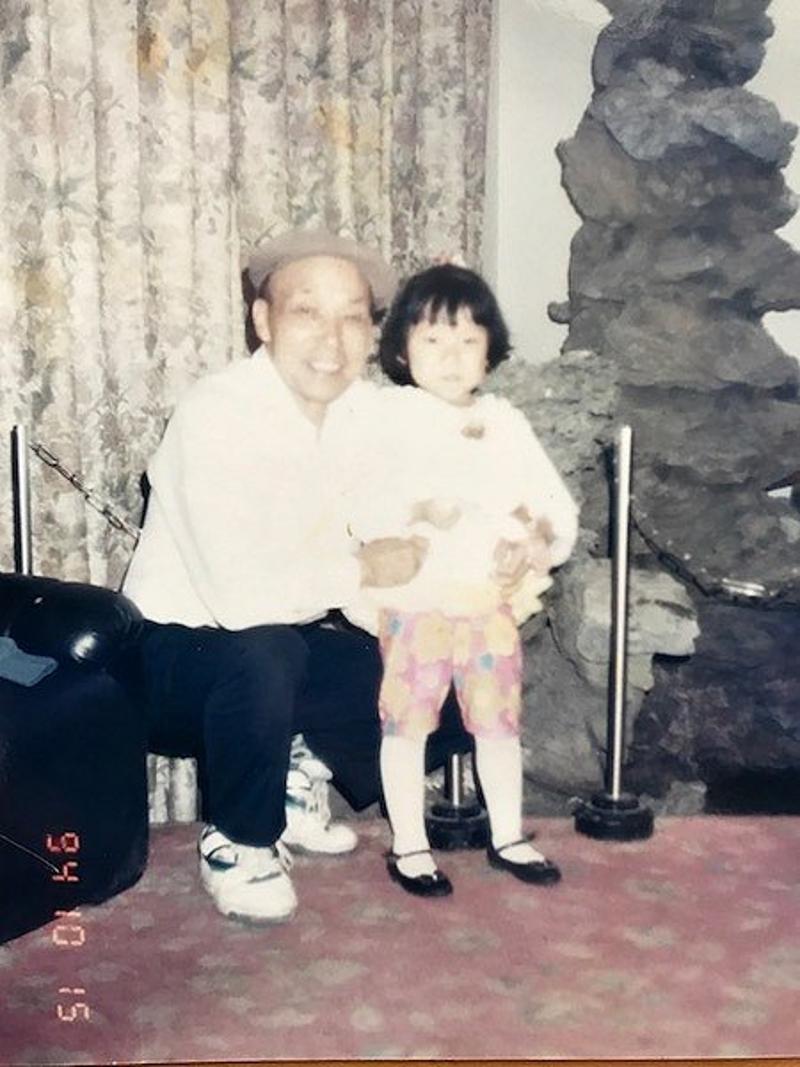
我印象里,爷爷只在他84岁本命年的春节穿过一次新衣服。一件姑姑买给他的红色羽绒衣。看得出来,他挺喜欢。他只在见重要的亲朋好友时才会把这件衣服穿出来。而实际上,尽管衣服有点鼓,显得他的头特别小,腿特别细,但红色真的还挺适合他。记得三十那天,我就看他好半天——可能是因为太新鲜了。他察觉后问我,“是不是穿红色好看很多?”语气里有种他赢了的感觉。
再后来我就出国念书了,好几年没能再在家过年,也就不知道爷爷是否再有穿过新衣。可爷爷却没有放松丝毫对我的盯梢。和他拜年视频或者电话时,他总会说,“你啊你,又调皮捣蛋地过了个年”。
前年年中,我回国开始工作。那年春节前,我为自己买了一件正红色的卫衣,胸前还有品牌大大的猴子商标——那年恰巧是猴年。那是我上初中后再一次在年三十穿上红衣服。
不出所料,家里人给予了我的红色新衣一致好评。不过,我没能得到爷爷的夸奖,他在我回国的第5天离开了。
命数的事,纵然再难舍难分,也只能慢慢习惯去接受——现在,我也习惯了过年时,穿一件红。
32b4ae64-4730-43aa-9bb2-18257fb8cc56.jpg)
dfd7e41f-438a-40e8-b3c4-a40a6fd7ce73.jpg)
136c3bd5-f1af-4998-a829-69d7e916036f.jpg)
c5fcf75b-5786-44b4-b003-26e70a4ba43d.jpg)
6028ebb4-2fb1-4be1-bd2d-497470004bf8.jpg)
1cdc2eaa-ee2f-479f-b896-3722e4229d1b.jpg)
d3fa5b6d-12f3-49e9-8157-207ac5428c4d.jpg)
3f82b564-7e71-4a6a-8d5a-82fe90845ef5.jpg)
467fc0b9-ce22-4c89-a46d-90ba776af3b2.jpg)
ce4e2e70-135c-479a-815e-21ee79d51954.jpg)
0e005807-1df5-4d5e-97b1-ad9a48eb8558.JPEG)
11df0ac5-b5d5-469d-9062-3961c5a19ac5.jpg)

232c0d4d-c0f3-440c-b243-801e3cc994c5.JPEG)
7dd9c3fc-5c44-44e4-a69b-a6ee4e1305c3.jpg)
4e8ac3d6-5841-4859-9b63-5bb7cc734d9b.jpg)
6a2cd031-0edb-450d-acf6-e32580002929.JPEG)
fbaa0973-c1f6-4be6-b553-408ca4c02c26.jpg)
381043d7-6b33-4915-ad76-4fed3c5c6d5f.jpg)
ec564b61-64b6-4702-b71b-799e3f34938f.png)
ef3f2590-ecec-45f9-a33e-5d422d2e0cda.JPEG)
93f2e302-9313-49d4-a786-44066ee40b90.jpg)
128177d7-4aac-47f7-8d4b-e7b50e7f65ff.jpg)

0d93b615-a026-45f0-9362-95a3a296ec27.jpg)
4a527350-3b68-4d29-8b4a-be8699cbe511.jpg)
4681fd99-3643-45ca-b7e7-53f13e209201.jpg)
c74774d4-92c6-424d-b9b7-1707ef2978c8.jpg)
7ff29a2c-a2f1-4acf-b967-cfbc7afee8d7.jpg)
131588f3-4e93-422d-9f1a-f8861f3d4891.jpg)
adaa4974-9e51-494f-97dd-9b33e79cba36.jpg)
219d2994-99d2-4839-b49f-1ef7ad06125d.jpg)
a5a4ebc4-5a94-49bc-ab75-b417321ec76e.jpg)
21ec19d7-b12c-4647-9c26-d4456a59ad0d_zsize.jpg)
6a3f8845-91e4-4c81-bb94-a34a7878825f.jpg)
06991316-2c52-4086-9cad-7138ac7a4579.jpg)



f7dc3e69-a8f2-4799-9491-e84fad24fc07.JPEG)
9da7e9e9-af81-4603-a756-6895d5f113e6.jpg)
8da75b4d-3d45-4015-9948-af79a839ac21.jpg)
79658a21-5099-449b-801d-a61969551e83.jpg)
17a798e7-12a5-43e3-b92a-ba28db87526a.jpg)
d41ba343-dd9c-4e1e-952e-ae00fd657060.jpg)
ea78dca2-0d77-4ee3-a471-d70a1569233b.jpg)
226662c4-994e-40f5-9701-bff5ec80cf13.jpg)
7c1db895-d3f8-4e1e-9768-25257cc7e499.png)
7b0e2f7b-cef6-4079-b7f4-f7715f74556d.jpg)
9c9d7f2e-e29d-4a57-b50c-4077225c0104.jpg)
d6a121e6-ef73-4eca-898c-26a53fa79ef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