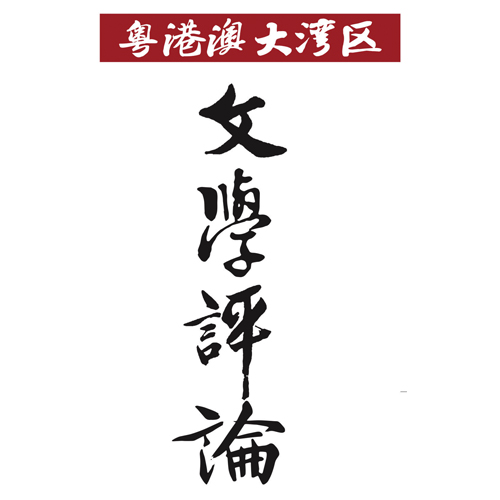程光炜: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

一
九十年代以来,因受后现代哲学影响,以及文学史自身调整原因,中国现当代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渐成热潮。
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主要作家的权威性被重新讨论;二是这些作家思想和作品的主要方面被忽视,次要方面成关注点,比如鲁迅的“国民性”被转换成“个人”,《野草》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重要性,俨然超过了他的小说和杂感。有一段时间,“症候式分析”也热络起来,状态、暗示和隐密心理被曝光,作品成为作家隐私的承载。例如茅盾1928年流亡日本期间的私生活,曹禺的婚姻,巴金致萧珊的书信,老舍访谈录,等等。这些次要材料信息,能丰富原有材料库存,增加作家形象的立体感,然而,损毁、暗伤的负面效应也未幸免,不能不令人担忧。
对于讲究道义形象的国人,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不习惯这些主要作家的“私人形象”出现在公共空间,大家会为之惶恐。但是,历史转变从来不会止于意识层面,它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这对几十年习惯于正襟危坐的人们来说,心灵所感受的冲击确实不算小。
如果依文学史自身的调整看,积极方面说,在“新文化论”“启蒙论”之后,人们愿意“回到鲁迅那里去”,强调文学的自主性,作家研究不被其他东西牵累,这当然明显加大了对作品文本内涵的研究,丰富了文学史课堂,加强了学生的审美教育。不足也存在,当历史的连续性被断裂、问疑,或是这种历史覆盖了另一种历史之后,学生会出现历史失重感。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历史失重感,一般都出现在历史转折之际,比如1949年、1979年、1985年、1993年等,真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1978年春,大学的现代文学史课堂上,贯穿始终的是“鲁郭茅巴老曹”“左联”,革命文学,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之争,“第三种人”,最后再挂着赵树理、丁玲和周立波的土改小说。文学思潮是文学史主要讲授内容,与之搭配的当然是主要作家和主要论争等。自然,不曾出现过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名字,学生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些作家。我是在毕业很久之后,才读到他们的作品,知道其人在文学史上的存在。他们后来,都是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先后重返文学史叙述之中。所以我担心,当历史出现再次断裂,在读学生是不是会感觉“鲁郭茅巴老曹”,也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会看轻鲁迅,还有他那些异常沉重的作品吗?这种担心在樊骏先生的精确统计中已经显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10年间,在出版的40期《丛刊》中,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文章近500篇,接近全部论文的一半。它们是:鲁迅46篇,老舍28篇,茅盾、张爱玲各17篇,郭沫若16篇,巴金、郁达夫各15篇,沈从文14篇,周作人、萧红各13篇……鲁迅保住了头牌地位,老舍基本正常,茅盾被迫与张爱玲并列,沈从文、周作人对郭沫若、巴金急起直追,已现“逼宫”的气息。研究尚且如此,文学史课堂教学还不很快跟着走,将信息传布到学生那里去?
……
四
文学史研究也对上述热潮做出了响应。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主要作家地位,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以主要作家为重,到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沈从文被列入专章分析作家,在第二编中,与茅盾、老舍、巴金和曹禺并立,与他们的页码也大致相当。沈从文一章,明显采用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某些观点,比如,肯定了作家将“残酷”“愚昧”描写转化为人性美的观照,相信他对农民、士兵、水手、下等娼妓、童养媳、小店伙计的正面叙述,确实展现了人类生命的自在状态等等。王瑶在为其所做的“序”中,主要作家意识也有软化,认为作者吸收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写出历史的全貌。”
这等于承认了随着历史转折引起的巨变,主要作家范围、阵容和对象日益扩大的事实,也默认了该书对主要作家某些边缘研究的现状。当然,与我列举的主要作家边缘研究的典型例子相比,这部著作的边缘研究走得不远,而试图显示出稳重、适度的叙述风格。
可见,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并非上述几个典型例子,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曾经大范围发生的现象。这一现象,从文学史研究方法、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到文学批评的勃兴,无不涉及。它从八十年代初持续至今,少说疑有近四十年的历程。它对这个学科的深刻影响,已非一篇文章所能涵括、评估。这次提出,无非是说一个持续多年、习焉不察的文学研究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边缘研究”尽管并非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发展的全部面貌,但边缘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习惯的影响却很长远,不能不引起不安。比如,翻开现代文学研究杂志,对传统的几个主要作家的研究兴趣不再,即使鲁迅仍受关注,但大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反倒是他思想和作品的边缘成果相对时兴,如鲁迅与版画、某种作品版本的源流及考证、作品人物索隐等。鲁迅研究的高度和深广度,已不复存在,像丸山昇这种发人深省的研究,几乎无人延续。
当边缘变成一种知识结构,变成一种思想视野,那么就会妨碍对主要作家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提升。我这几天无事,翻阅了茅盾八十万言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再次读到他与大革命、抗战和以后历史的广泛复杂的联系,也可以说是深度介入,感慨良多。比如从武汉革命风潮中脱离,比如新疆出逃,再比如三下香港避难等,真是惊心动魄,不可复制。他们那一代作家,因为历史关系,都无法脱离与历史这种长期、复杂和深度的纠缠。他们的作品在见识上,也因此高于前一代和后一代的作家。过去的茅盾研究,确实存在与历史的政治结论过于重叠的问题,没有超脱出来,因此不妨说,现在也不是没有茅盾研究再出发的可能。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是少有成果之一,可惜此类著作太少。
在这一看似漫不经心的过程中,边缘还会使主要作家的原有东西被慢慢磨损、萎缩、变质,不再影响研究者的思想境界,不再显出研究的高度。它进入了历史遗忘的程序,在下一代人身上,在接连不断的文学史课堂讲授中,在人们的记忆里。我对此就有一个经验。我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或让学生做七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时,发现他们在处理历史问题的过程中,难以避免“抓小”“放大”,这固然与其历史经验有关,其中也不乏如上面所说,主要作家原有东西被磨损、变质之后,就会不自觉传输到学生这里,影响甚至放低他们的思想境界。由此写出的文章,也许会显得小气,局促,浅显,叫人不安。
由此可见,对“边缘研究”的已有成果不能小看,对它的影响、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也不能视而不见。目前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没有新时期以来的“边缘研究”的历史评价这个题目,如果设立,真可以坐下来做上几年,想必会给人们一点新的启示。
从九十年代孵化出的“边缘研究”,有它正面的价值,如对以前宏大、单调研究的润滑和调整。消极的方面也不能视而不见,如本文所说的那些现象。九十年代在某种程度上给人自由的感觉,然而也不能说没有代价。它的进展伴随着某种混乱,它的反思孕育着短小、局促,它的推进中也有欣喜、惊奇,比如多年不见的书籍因此问世,之后这类书籍再没有见到,也是不能不说的一件事情。
(本文系节选,注释从略,完整版请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近年来,专事于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主持“重返八十年代”讨论专栏,并承担北京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代表著作有《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艾青传》等。主编有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