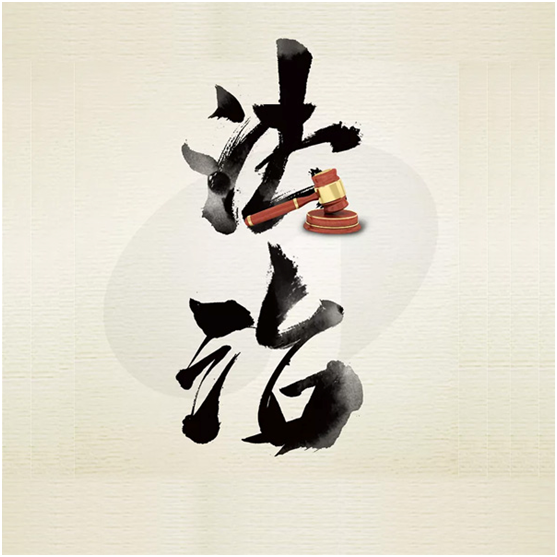南方+对话破产法学专家:个破首案将为全国性个人破产立法提供依据
7月20日,我国境内首宗个人破产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裁定宣告审结,35岁的深圳市民梁华明(化名)成为我国境内个人破产第一案的申请人。
“个人破产”首案备受大家关注。首案对对探索未来个人破产制度有什么指导意义?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个人破产”制度还有哪些“关”要闯?我们该如何期待“个人破产”的未来?带着这些疑问,南方+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阳光教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
1、南方+:个人破产条例出台后,大家十分关注“个人破产”首案的动态走向。在您看来,“个破”首案对探索未来个人破产制度有什么意义?为何它如此重要?
徐阳光:任何一个新的法律出台,第一案都是备受关注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作为我国个人破产试点立法,在社会各界并未就个人破产制度达成广泛共识的背景下,该条例实施后的第一案无疑备受瞩目。
在我看来,深圳个人破产第一案意义重大。
首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性质的案件,它标志着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开始从无到有,进入真正的司法运行阶段。
其次,第一案在破产申请、审查、受理、审理等环节都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社会各界学习和认识个人破产制度的标志性案例。透过该案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破产,法院在什么情况下会受理破产申请,法院如何选定管理人,法院如何审理个人破产案件,个人破产管理人、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如何依法履职。
再次,该案是个人破产重整的案件,可以让我们看到个人破产重整与企业破产重整的差异性,更加明白个人破产制度的重要性。最后,第一案的成功审理必然会增加社会各界对个人破产立法的信心,有助于破产文化理念的普及,为今后全国性个人破产立法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2、南方+:《条例》的初衷是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实现经济“重生”的机会。“个破”首案的案例是否符合“诚实和不幸”的原则?于当事人而言,“个破”能解决帮助他们什么问题?
徐阳光:从本案审理的结果来看,法院基于债务人的申请材料以及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状况和破产前交易状况的调查,应当是得出了债务人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的结论,故而允许债务人通过破产重整程序来获得余债免责的破产救济。这也是条例立法目标在个案中的具体实现。
该案中的债务人因投资创业失败面临债务困境,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并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个人和配偶的收入来尽可能地偿还所负债务,避免了被债权人频频追索之讼累甚至是被各种形式逼债之痛苦。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层面的救济。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条例的规定,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之后,就解除对债务人的行为限制措施,债务人在免责考察期结束之后即可豁免剩余债务,这些都为债务人走出困境和走向新生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生动体现了个人破产制度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全新开始”的立法追求。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债务人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投入到创新创业的进程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因此,这个案例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对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个人破产制度可以为其提供财务和精神层面的多重救济,可以尽快给予其“全新开始”的机会,可以让债务人尽快地恢复为有生产力、有创造力的社会成员,进而增进社会整体福祉。
3、南方+:“个人破产”条例出台后,许多人担心“个人破产”会成为“逃废债”的工具。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徐阳光:我知道,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对个人破产制度没有信心,担心债务人借个人破产程序达到逃废债的目的。实际上,只要认真研究过个人破产制度,认真看一下深圳的个人破产条例,就知道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忧。
首先,条例为申请人设定了严格的申请条件,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会被法院裁定受理。前些日子深圳中院做出了条例实施以来的不予受理个人破产申请的第一案,为如何厘定不予受理的标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其次,进入个人破产程序的债务人,必须如实申报财产状况和负债情况,管理人或破产管理署还会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破产前的交易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这既是防止债务人转移、隐匿财产、虚构债务情形的发生,尽可能地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同时也是为了识别债务人是否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进而确定是否批准免责。
再次,条例综合比较域外个人破产立法经验,选择了许可免责的立法模式,并将债务清偿比例与免责考察期挂钩,可以有效防止免责制度滥用的风险。
最后,条例第103条还特别规定,债务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债务人通过欺诈手段获得免责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免责的裁定。这是打击借破产程序逃债的行为的有力手段。
因此,我们的立法已经尽可能考虑打击逃废债的行为,再加上破产撤销权、无效行为制度、非正常收入追回制度,这些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都没有的制度,可以更好地打击逃废债和保护债权人利益。我们一定要对个人破产立法有信心。
相反,缺失个人破产制度的社会,不仅企业破产法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实施,反而让债务困境留在社会无法解决,使得以个人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无法彻底终结,抢先执行、哄抢财产、暴力逼债的现象也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
4、南方+:该案的破产管理人感叹,个人破产比企业破产难做。对此,您有何看法和建议?
徐阳光:关于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履职问题,确实与企业破产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对债务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可能更加艰难,在涉及家事关系、住宅处理方面会遇到很多挑战。
这也告诉我们,破产管理人不能指望仅靠企业破产中的履职经验就可以做好个人破产案件,应该加强对个人破产制度的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技能和综合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发挥破产事务管理署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的作用。英国的个人破产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法院的主导下充分发挥破产管理人和破产事务管理机构的合力,才能真正办理好个人破产案件。
5、南方+:我国“个人破产”制度走出了第一步。未来,“个人破产”制度还有哪些“关”要闯?我们该如何期待“个人破产”带来的变化?
徐阳光:展望未来,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有效实施,必然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但也会面临更多的难题和挑战。
法院如何进一步厘定受理或者不受理个人破产申请的标准?法院如何在指定管理人的过程中更好地考虑债权人的意愿?法院或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如何加强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培训、队伍建设和行业自律工作?如何建立更好的调查机制来识别“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如何准确适用豁免财产的规定?如何正确行使免责裁量权?重整与和解程序如何区分?庭内和解与庭外调解如何有效衔接?等等。问题肯定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但我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我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首先,法院应当加大对个人破产案件审理的人力支持,培养法官的专业能力,以应对可能增加的个人破产案件数量。
其次,法院应当关注各类案件的特殊性,对关键节点和重大问题进行专业讨论和论证,对成功案例和好的经验及时总结宣传,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再次,法院、管理人、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应当积极作为,各司其职但又要密切合作。最后,对一些囿于条例位阶难以克服的难题,也应当及时梳理总结,以供未来全国性个人破产立法研究和解决。
【撰文】邓子良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