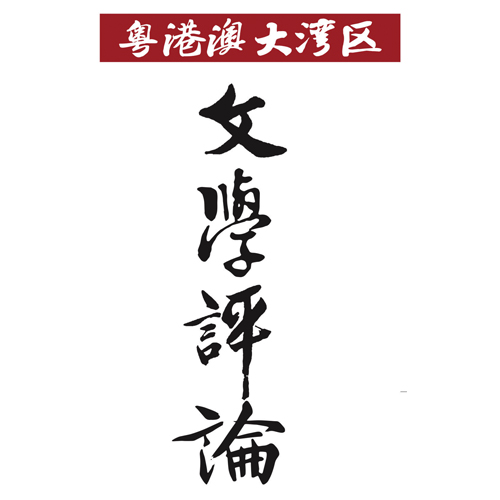张均:当代文学中的青春与革命——重读《三家巷》

在目前有关《三家巷》(1959)的文学史评价中,涉及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中共革命与岭南地方文化的“广州记忆”占有突出位置,新世纪以来相关影视改编(如电视剧《风雨西关》、粤剧《三家巷》等)也往往由此入手。不过,可能因为自己生长于农村之故,我对这部以广州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较少共情。其阅读亲近感受,大不能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相比。当然,《三家巷》却有其独特的、难以被替代的文学史贡献。这包括两层:一是《三家巷》对青春问题的发现与建构,二是它对革命问题的理解与处理。《三家巷》在这两个层面上经验发现与叙事建构的价值,都要重于“广州记忆”,更值得细加探究。

上 青春与“大历史”
《三家巷》扑面而来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大革命”背景下一代青年喷薄而出的青春。小说写道:“(这时)有六、七个年轻的中学生从官塘街外面走进三家巷来。头里走的一对是周炳的二哥周榕和陈文婷的二姐陈文娣,跟着走的一对是陈家的大少爷陈文雄和周炳的姐姐周泉, 其次是陈家的大姑爷张子豪和何家的大少爷何守仁,最后是一个年纪最大,个子最高,国字脸儿的同学,叫做李民魁的。他们在这个暑假期间, 经常晚上游逛之后,到三家巷来乘凉,一面谈一些国家大事,一面谈各人的未来的梦想。”(《三家巷》,第 31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年版; 以下皆同此版本)《三家巷》所叙,即是这批青年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青春史。与现当代文学史上多数以青春为主题的小说一样,《三家巷》中的青春,亦非赤裸的无所依附的青春:这是一群被现代中国建构实践所冲击并参与这一实践的“新青年”。他们的青春也是当代文学青春叙述传统的一部分:“青春就是飞扬的,是不受传统拘束和规则压迫的。无论是王蒙的《青春万岁》还是杨沫的《青春之歌》,青春都是这种革命话语下的‘冲破’‘打碎’和‘前行’的形象;而新时期以来,《人生》的‘忏悔面孔’与《摇滚青年》的‘现代面孔’,赋予‘青春’忧郁的历史气质和未来想象的现代性意蕴。”显然,《三家巷》,不是这种青春叙述传统的开创者。在它之前,不仅有《风云初记》《保卫延安》《上甘岭》这类同时代“前文本”,而且还存在着《莎菲女士的日记》《家》《财主底儿女们》等久远的文学史记忆。对此,夏志清一语道破:“在(《三家巷》)前半部,作者不但对五四时代的青年, 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和了解,而且在描写他们的态度和理想时,笔触是一种怀旧式的写实,令人读来兴味盎然。”究其实质,《三家巷》之“新青年”与此前“五四时代的青年”们,具有高度相似性:他们都是尼采所批评的“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与现代中国诞生史同构共生之人。他们是“大历史”(History)的产物,更是“大历史”的实践者与创造者,恰如小说中陈文雄沉着有力的宣告:
为什么青春那样可贵!咱们有能力,有青春,有朝气,那是锐不可当,无坚不摧的!咱们看三十年之后吧!到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也就是到了后半个 20 世纪,那时候,三家巷,官塘街,惠爱路,整个广州,中国,世界,都会变样子的!那时候,你看看咱们的威力吧!世界会对着咱们鞠躬,迎接它的新的主人!(《三家巷》, 第 61 页)
这样的青春显然与新世纪以来文学中的青春迥然相异。后者(如《致青春》等怀旧电影)是“去历史”的:其中“所谓的‘大历史’都被简化或淡化处理了,个体化的、细节化的、偶然化的、平民化的、生活化的‘小历史’(history) 凸显出来”,这“不是指这些影片没有历史,而是指没有‘大历史’;不是说个体的生活中完全缺失‘大历史’,而是说‘大历史’与‘我’无关,与‘我’的生活内容和关注点相距遥远,因而成为‘异己之物’。” 欧阳山对青春的理解不同于此。他几乎希望《三家巷》中每一青春细节都融溶在“大历史”中,成为历史整体性与总体性的具体构件。周榕、陈文雄、周炳等“新青年”,用“大历史”眼光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时代,并在历史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主体位置。
就此而言,《三家巷》是当代文学中一部合乎常规的作品。不过,“常规”恐怕并非欧阳山的追求。即便在 1950 年代,《三家巷》的青春叙述也力求有所突破。依笔者之见,《三家巷》在呈现“大历史”视野中的青春时,有两层突破的努力:(1)青春与家族的嫁接;(2)青春的历史分化。尤其是后者颇可见《三家巷》异乎寻常的深刻。

与《青春之歌》《红岩》等不同的是,《三家巷》的青春叙述完全置诸家族框架完成。小说给人的感觉,“大革命”前后的广州与中国,似乎都凝聚在何、陈、周这三户人家子弟之中,所有日常生活与重大事件都围绕着他们而展开(兼带地还涉及胡家、区家)。这当然是有意设置的结果。究之现实,广州并无一条真实的“三家巷”,下层出身的欧阳山也不曾结识何、陈这样的富贵家族。《三家巷》的家族设置,更多是向古典文学(如《红楼梦》)积极借鉴的结果。
不过,《三家巷》有关青春的历史分化的叙述却有其不可复制的社会深度。这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对“新青年” 群体分化的深描。出现在“三家巷”中的一批意气风发的“新青年”,短短数年即在剧烈时代变化中走向分化与决裂。若论青春的聚散,《家》《青春之歌》《白鹿原》都曾涉及,但《三家巷》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最大气力刻画了“新青年” 分化的深刻社会结构原因。“新青年”们的短暂“同路”和最终分道扬镳,不是因为诡谲难测的天数,亦非因于思想认识的不同。后者,是《家》《青春之歌》《白鹿原》所认定的青年分化的主要根由,但在《三家巷》中,思想分歧虽然存在, 但却是结果而非原因。那么,原因何在呢?这在这群“新青年”刚出场时就已见端倪,如在讨论如何救国时,“把旧的政府,旧的社会,旧的家庭,旧的人格,通通给它一个彻底摧毁”“振兴实业”一类“谋略”都得到呼应,但周榕有关“办好工会”“替他们(按:劳工)争一争待遇”的建议,立刻就遭到反对:
李民魁和张子豪还没说话,何守仁就抢先驳斥了。他使唤恨恨的,不友善的调门说道:“那怎么使得?那怎么使得?周君虽然有仁人志士的心肠,但是太偏颇了,太过激了!”(《三家巷》, 64 页)
这意味着,姻亲、表亲、同学等关系,都不及现实利益考量重要。位置决定想法,地位不同、利益考量不同的人在抽象问题上或可虚应故事,但一旦涉及具体现实问题,便不能不是敏感而不宽容的。周榕与张子豪等的争论在表姐妹中也发生了。对于工人是否重要的问题,商人家庭出身的陈文婷和来自做工家庭的区苏同样互不相让。这些当然不是意气之争。实际上,倘若处境不同、诉求不同,个体的世界观及人生选择自然会相去甚远。张子豪、陈文雄等之所以不赞成周榕的革命言论,并最终走上与周家、区家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主要不是因为思想观念之异,而是有着切实的实际利益考量。小说写道:“李民魁在国民党党部里面做事,穿着中山装,浑身上下,都闪着棕色的马皮一般的光泽;张子豪从中学毕业之后,又进了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出来当了军官,因此穿着姜黄色呢子军服,皮绑腿, 皮靴,身上束着横直皮带。这两个人都十分神气。”(《三家巷》,第 95 页)等到张子豪当上连长以后,他的生活消费立即升级:
(他)把旧房子退掉,另租了一幢新洋房的二层楼居住。这里是朝南的一厅三房,十分宽敞。旧的家具都卖掉了,换了全新的藤制和杂木家具。他和陈文英都换了新衣服,他们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叫做张纪文的,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叫做张纪贞的,也都全身上下换了新衣服。连招待客人的“雅各”牌饼干,“新基士”金山橙子, 伦敦制造的杏仁奶油糖果,“斧头”牌白兰地酒等等,也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像这一家人是刚从别的星球来到广州似的。(《三家巷》, 第 149 页)
对此,陈文雄说得一针见血:“大姐夫为什么拥护蒋校长?道理很不复杂:这房子、家具、衣服、食品,蒋校长都给换了全新的,连我这两个小外甥都重新打扮了,为什么不拥护?”(《三家巷》,第 151 页)在现实中,心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高尚之士”总属稀少,大多数人都未脱出黑格尔的断言:“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即便是《三家巷》中“有朝气”“锐不可当”的“新青年”们也不例外。奥威尔曾将人群分为三类:“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他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细细考量,《三家巷》中“新青年”们除个别人物外,大都并未脱出黑格尔、奥威尔之于人性的深刻观察。这无疑接近普遍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敢于、愿意背叛自己群体利益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身体比语言更诚实, 他们最终都会选择于自己有利的道路。而陈文雄、张子豪、周榕、区苏等“新青年”们既然在社会上所居位置、生存处境各有差异,那么他们最终的疏远、分化就是必然的。

这几乎是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发生的故事,《三家巷》忠实地呈现了它。这也是“大历史” 视野的结果。“大历史”视野不仅是对于历史变迁的整体性、总体性理解,也包含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介入当代作家“深入生活”实践以后所形成的唯物论眼光。在《三家巷》中,利益考量与理想信仰之间的冲突,对于意气风发的“新青年”们而言,这又是青春、成长中的撕裂与阵痛。其势不可遏,且多和爱欲相互背离,由此构成了生活中最深的苦痛。用陈文婷的话说即是:“一个社会好好的,有家庭,有亲戚,有朋友,怎么一下子就能划成四分五裂!”(《三家巷》,第 188 页)在当代文学中,能将青春在现实“大历史”中的撕裂表现得如此及时而深入的,少有能和《三家巷》相比者。《三家巷》所以能够如此,与欧阳山的坎坷身世是有关系的。欧阳山出身贫苦:
养父是个小职员,常常失业,赋闲在家,曾到北京、西安、镇江、上海等地谋生,欧阳山从小就跟他到处奔波,四处流浪,这种穷愁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欧阳山接触过很多下层社会的穷苦人,开始认识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显然,久处下层社会、长期深陷困境的欧阳山,并不迷信观念的力量。《三家巷》因此与《青春之歌》《白鹿原》差异甚大。《青春之歌》中的白莉苹、王晓燕、李槐英和林道静,或殊途或终同归,主要因于观念认识的深浅有异,《白鹿原》中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等幼年玩伴后来踏上迥异人生,也主要出于信念差异或变化,但在《三家巷》中,强硬有力的利益关系,犹如一把利刃,剖开并击碎了那些一度以整体形态出现的青春。
当然,从“重写文学史”眼光看,《三家巷》的此种深刻,源于“阶级意识的兴起打破了三家巷的平静安宁,情同手足的三家巷小儿女由此走向分裂,亲情、友情和爱情都将接受阶级意识的洗礼。对于周炳、周榕等从“新青年”群体中的离析而出,《三家巷》的叙述就显示了它的深刻:周炳兄弟走上革命之路,主要来自他们自己在生活中的磨砺和思考,如“对于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是否应“摧毁整个旧社会”“重新建立一种美好生活”的问题,是区桃牺牲以后周炳所产生的“新的想法”(《三家巷》,第 142 页)。此外, 他想从打铁铺、手车修理店、裁缝铺子、糕饼作坊、皮鞋作坊里“多找几个人”“跟咱们是一模一样的人”(《三家巷》,第 283 页)的想法, 也是他在经受现实挫折以后想到的。以此而论,《三家巷》是重返了阶级论最初的文学史时刻: 它是对“五四”以来“大历史”视野的承续,更是对它的反抗与突破,是立足于唯物论眼光的对于世界的重新发现。
(本文系节选,注释从略,完整版请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第三期)
【作者介绍】
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高层次青年人才。入选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2012),两次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5、2018)。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等专著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研究课题。近年学术志趣主要集中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