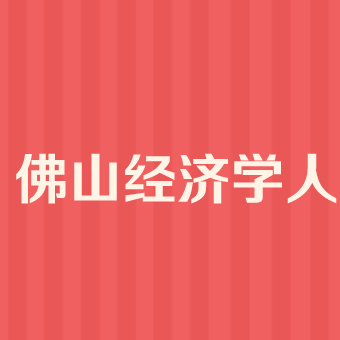南方特稿|溢达在新疆:一位香港女企业家的寻棉“西游记”
在杨敏德很小的时候,身为香港“纺织大王”的父亲杨元龙就跟她说:“你一定要记住,要是没有人种棉花,你就没饭吃。”但是恐怕杨元龙也没有想到,他的女儿后来竟跨越千山万水,跑到祖国最西边的新疆去种棉花。
2021年3月,在一片“力挺新疆棉”的呼声中,由杨敏德执掌的溢达集团(下称“溢达”)走进大众的视野。这家来自香港的企业,于1988年进入内地落户广东佛山,并于1995年起在新疆建设棉纺厂。日前,运动品牌李宁因印在服装标签上的“新疆棉”而屡获点赞,实际上,其“幕后功臣”正是溢达。
过去26年来,依托优质的新疆棉花,以及佛山等地强大的制造能力,溢达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制造商之一,其产品出口至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全球各地,是世界众多知名时装品牌的面料和成衣供应商。
这背后,藏着杨敏德和溢达在新疆长达26年的耕耘。这是一个香港女企业家不远万里前往新疆种棉花的故事,是一家企业依托新疆棉花成长为世界顶级纺织巨头的故事,也是一个纺织企业与新疆棉农合作共赢的故事。

在还没有继承父业执掌溢达时,杨敏德就已经在耳濡目染中继承了父亲对寻找好棉花的执念。
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后,香港纺织业开始兴起。从美国纺织学院毕业的杨元龙,在回国后便带着家族财富投身纺织业,并且很快成了香港“纺织大王”。
1978年,杨元龙创立溢达集团,适逢中国迎来改革开放,怀揣实业报国心愿的杨元龙,率先进入内地设厂。溢达成为最早进入内地的香港纺织企业。之后,杨元龙又与内地签成了首份贸易补偿协议,并将中国制造的成衣卖到美国,做成了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第一笔生意。
到1980年代,杨元龙加大在内地投入,耗资4亿多美金在佛山高明建设了溢达纺织,成为当时内地设备最新、收入最高的纺织企业。
在杨敏德记忆中,功成名就的父亲一直有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制造一件纯棉免烫白衬衫。这看似简单,但是,一直到了1980年代,杨元龙绞尽脑汁也没能达成心愿。
“最大的困难在于衬衫的原料——棉花,质量必须是顶级的,足够纤长柔韧,这样纺纱后织出来的布才更耐蚀,制造出的衬衫才能经受得住免烫处理。而如此优质的棉花,实在太难找了。”杨敏德说。

杨敏德。图源自网络视频截图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年事已高的杨元龙,带着“纺织大王”的荣誉与心愿未了的遗憾,正式退休。杨敏德接班,成为溢达的第二代掌舵人。她接过了企业,也接过了完成父亲残念的重任。“做好一件纯棉免烫白衬衫”成为杨敏德的执念。
但摆在杨敏德眼前难题,依然是棉花,优质的棉花,大量优质的棉花。
当时,世界上只有四个地方可以出产杨敏德所需的优质棉花,分别是埃及、秘鲁、印度和苏丹。但是由于产量和战乱等种种原因,几无可能从这些地方进口优质棉花,更别提获得持续稳定的产能供应。
正当杨敏德茫无头绪之际,一位日本朋友指点迷津︰“新疆有呀!”
地处中国西北角,距离香港4000多公里的新疆,对杨敏德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那个互联网还未兴起的年代,杨敏德无法从网络上获知新疆棉花的情况。对棉花的渴求让杨敏德决定从香港前往偏远的新疆,一探究竟。
这是一趟充满惊喜与波折的旅程,杨敏德形容其为“寻棉西游记”。在新疆,杨敏德如愿找到了从父辈就开始苦苦追寻的好棉花——生长在新疆的长绒棉不仅洁白柔软,并且拥有更细长强韧的纤维,做成的衣服在亲肤度、舒适度、弹性和光泽方面都更优越。
但是,当时新疆的棉花产量也有限,并且内地对棉花实行限额分配,并不是有钱就能买配额。杨敏德一行从乌鲁木齐一路走到了靠近边境的喀什。一路上,她深感新疆棉果然优质,但当地纱厂的技术和机器都相对落后,她萌生了在新疆建纱厂的念头。
然而,没有配额,一切都是幻想。从喀什再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杨敏德已经做好了两手空空回香港的准备了。没想到的是,事情峰回路转。
在乌鲁木齐的饭店,一位在此等待已久的吐鲁番男士向归来的杨敏德招手,杨敏德听到了数日来最想听到的话。
他说:“小姐,且慢,我有限额分配批文。”

“纺织大王”的女儿要去新疆吐鲁番建纱厂了,消息传回香港,令业界大为吃惊。
杨敏德内心其实也有犹豫,拿到了配额并非就打开了“月光宝盒”,她面前至少有两大难题。一是技术难题,吐鲁番以火焰山和哈密瓜闻名,该地日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哈密瓜特别鲜甜,但是种出来的棉花却会因为糖分过高而过于黏稠,还会使纺纱机器严重受损。
“我也不知哪来的劲头,立誓要和这恶劣的气候,大战个三百回合。”杨敏德把自己当做了“取西经”的孙悟空。她观察到,当时,日本企业也在新疆收棉花,他们一定是想到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后来,通过向外请教,改良种植方法,溢达团队也成功降低了新疆棉花的糖分。
第二个难题是资金。杨敏德盘算着把香港一幢物业卖掉,把资金调到新疆。但这是一个重大决定,杨敏德不敢贸然行动,她先找到了自己很尊敬的两位世叔伯询问意见。最终,她得到了两位长辈的支持,其中一位长辈更说:“要是我年轻十年,也去新疆投资。”
考虑到背后的风险,杨敏德接受了长辈的建议,选择了更稳妥的办法,即把那幢物业卖掉一半,余下的一半还持续有租金收入。
从1995年起,溢达先后在吐鲁番、乌鲁木齐、喀什、阿克苏、昌吉成立了7家棉纺企业,总投资将近1.5亿美金。1998年,杨敏德在新疆喀什租了3万亩地,直接开始了种棉花之旅。

溢达纺织工厂。受访者供图
除了合作农场,杨敏德还带领溢达团队,直接与棉农打交道,亲自收购棉花。
当时,在新疆棉花收购市场,“打白条”(即欠条)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棉花收购企业资金准备不足,只能拖欠或者延期支付棉款。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棉农拿不到钱,无法继续投入种植棉花;另一方面,由于收购统一定价,不管棉花品质好坏,棉农因此也没有动力去种植优质的棉花。
为了改变这种不良循环,杨敏德决定率先在新疆实行不打“白条”的做法。在收购棉花之初,溢达提前备足了资金,直接用现金向棉农收购棉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坚持不‘打白条’,而且收购价是按棉花的品质厘定。
每年到了棉花收购的季节,溢达每天都会从银行提取300万至500万元现金,整齐码放在工厂内,用于向所有前来交易的棉农支付棉款。为了保证巨额现金的运送和保管安全,溢达为此还找到了专业的押钞公司负责现金押运。
一直到2015年以前,每天往返于银行与工厂间的运钞车都是溢达工厂的“标配”。直至后来越来越多的棉农开始逐步接受线上转账支付的方式,运钞车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这种现结现付的棉花收购方式,不仅让棉农快速回款,有足够资金投入下一年的棉花种植中,从长远看,对新疆的棉花产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农民是非常聪明的,你给他什么信息,他就怎么跟随你的价钱信息;你一家收棉花的不用‘白条子(欠条)’,就可以完全改变整个行业。”杨敏德说。
在溢达的推动下,过去那些实力不够,需要“打白条”的企业渐渐退出行业,促使更多有实力的企业进入到新疆棉花收购中,加剧收购竞争,使得棉农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推动新疆棉花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也正因为推动了行业的发展,杨敏德获得了“棉花公主”的称号。

“我将来能够跟人家说,你一生做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我可能会说,就是跑到新疆去,买棉花不打‘白条子’。这可能是我将来觉得,自己做得最有一点作为的事情!”2018年,在央视纪录片《我到新疆去》中,杨敏德如是说。
这不仅是对溢达改变新疆棉花产业的自豪,更是对新疆棉成就溢达的认可。依靠高品质的新疆棉,溢达完成了从棉籽到衬衫的垂直产业链构筑布局。溢达也一路在全球市场高歌猛进,成长为年产成衣超1亿套的世界级纺织工业“巨无霸”。
相比芯片、计算机等高科技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但是要做到极致也不容易。溢达通过构建从衬衫、面料、辅料、纱线、到棉花的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做深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从而极大强化了企业对产品品质的控制能力,这也成为溢达的重要“护城河”。
其中,作为原料的棉花是保证品质最为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杨敏德父女两代人执着于寻找好棉花的原因。自1995年杨敏德在新疆找到长绒棉后,26年来,溢达一直坚持投入对棉花品种和灌溉技术的研发。
资料显示,2002年,溢达在新疆设立棉种培育基地,在业内率先开展棉花研究。为了缩短棉花培育的研究周期,溢达还将扩繁基地延伸至海南岛,使得种棉在南北两域实现一年两造培植,令研究周期缩短一半。

溢达纺织工厂。受访者供图
从2011年开始,溢达出资1600万元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基因组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共同开展研究项目。2015年,海岛棉基因测序研究项目正式完成,有效提高了棉花育种的效率和精度。
截至2020年,由溢达选育并被审定的海岛棉品种共5个,所有品种均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测试及认证。根据溢达介绍,新海棉是超长绒棉,因其纤维柔长且强度较高,被全球纺织行业认为是高端奢华产品的顶级原料。
除了在棉花品种上加强研发, 溢达还在新疆棉田采用和推广滴灌技术、减少化学品使用和实施可持续种植计划。新疆溢达棉农通过使用生物灭虫方法,较其他种植区少用两成的杀虫剂。这些创新举措不仅保有了新疆棉自然、洁白、健康的特点,也让棉农的收成与收入同步增长。
此外,与当地棉农达成的合作与信任关系,也成为溢达在新疆持续稳定收到好棉花的一个重要保障。其中,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溢达与棉农“签订棉花定价收购合同”的事情,让很多溢达新疆员工记忆深刻。
当年,由于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不少企业陷入订单减少、交期缩短、产品价格下降等不利局面,受市场需求不足影响,原材料价格也跟着下跌。这其中就包括棉花的价格,尤其是新疆长绒棉的价格,当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这导致了当地棉农的收入减少,打击了棉农种植长绒棉的积极性。为了降低棉农的生产风险,帮助棉农增产增收,并达到长期稳定地发展新疆长绒棉产业的目的,2009年,溢达与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的四个村庄签订了长绒棉种植、收购订单合同,合计涉及棉田总面积约两万亩。
对于签订合同的农户所生产的长绒棉一级、二级籽棉,溢达承诺将全部收购,收购价格不低于订单中约定的保底价格;而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保底价格时,则以市场价格收购,以确保棉农利益。
据溢达新疆员工回忆,当年收购棉花时,常有与溢达签订订单合同的棉农,会顺便带上甜瓜、西瓜等自产水果,送给溢达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过去26年来,从新疆“长”出来的面料与成衣,跟随溢达走向全球。数据显示,溢达海外营收占比将近80,溢达不仅是全球多个知名品牌的面料、成衣供应商,更是连续15年在中国男士全棉梭织衬衫出口额排名中位居第一。
但是,过于依赖外贸也让溢达近年来遭受了不小的冲击。去年受国际贸易摩擦和突发疫情的双重影响,服饰成了外贸萎缩最显著的产业链之一。溢达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外界甚至一度传闻溢达面临破产危机。2020年4月到7月间,溢达更是忍痛先后关闭了全球4个工厂,将收缩的产能集中放到佛山基地。
事实上,在收缩产能应对危机的同时,溢达位于桂林和新疆的生产基地建设步伐也并没有停下来。在调整生产机构的同时,在外贸受到重创的背景下,溢达也开始调整市场结构,开始着力发展内销市场。
2020年起,溢达启动了结构调整三年计划,包括3个方面调整:首先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大力发展自有品牌“派”和“十如仕”;其次,大力开发健康类产品;第三方面,将广东溢达的2千多个专利技术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向同行业推广,助力纺织产业转型升级。
十如仕岭南天地概念店内景。受访者供图
过去一年来,随着市场结构的调整,溢达两个自有品牌“派”和“十如仕”的曝光度大增。这两者都称得上是从新疆棉“生长”出来的品牌——自溢达开始进入新疆起,它们就一直坚持使用新疆长绒棉作为原料。
这两个品牌也延续了当初杨元龙“制造一件纯棉免烫白衬衫”坚持,“派”和“十如仕”两个品牌的产品都做得非常“专”。其中,“派”主要提供高级棉针梭织男女衬衫,“十如仕”则主打纯棉免烫衬衫。
2017年9月,“十如仕”的首间体验店在北京正式开业。此后,“十如仕”加快布局国内市场。截至目前,“十如仕”在全国已开设6家实体店和3家体验中心,同时加快了线上电商的布局。数据显示,2020年,十如仕品牌国内收入增长超过60%。
去年5月,“十如仕”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以“新疆长绒棉”为主题的新品发布会。现场,新疆阿克苏的长绒棉花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用无声的装点讲述着品牌与新疆长绒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今年1月,“十如仕”在佛山王府井紫薇港和岭南天地连开两店。
不过,虽然品牌旗舰店逐渐在全国各地“开花”,但最特别的还要数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旗舰店。实际上,与北上广深不同,新疆并不是“派”和“十如仕”的主要销售地,但是杨敏德却坚持在此落户一家旗舰店。这家店不是为了营收,而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们希望新疆的同事可以看见,自己的努力最后做出来的产品是怎么样的。”杨敏德说。
【撰文】林东云 叶洁纯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