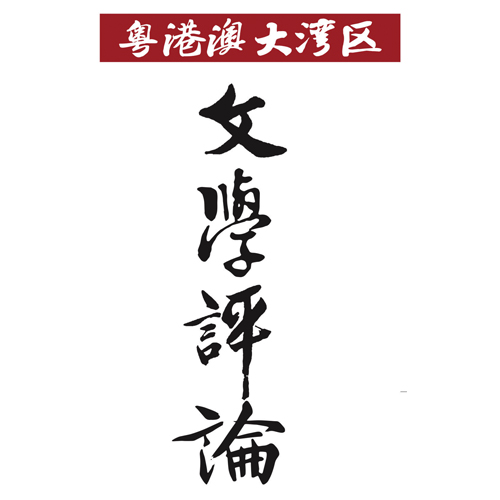李朝全:非虚构——报告文学的特质和创作方式

在文学体裁序列中,报告文学是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并列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通常被认为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已有100年历史。这是一种伴随着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从新闻脱胎而来的文学样式和种类,强调将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与文学进行嫁接联姻,从而产生出这种以迅捷反映现实事件和人物的文学体裁,因此有人称它是“新闻+文学”的产物,是新闻文学、艺术的报告、艺术的文告,等等。这种体裁的作品,重在记事写人、反映现实。从这一点上考察,报告文学实质上可以归入叙事散文范畴,是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但是,由于新闻的背书、新闻的背景,报告文学自然而然或者说是天然地具有一种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旨归的创作价值取向,也就是“非虚构”的创作要求。所谓的非虚构,从创作手法和价值取向上看,它大致相当于不虚构、无虚构、否虚构、反虚构,正好与虚构相对立;从内容属性和可信性上看,非虚构大致相当于客观、真实、可信。这是报告文学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质。脱离了客观真实,脱离了非虚构,报告文学就失去了生命,因此,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非虚构是报告文学的底线。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追求的是一种总体性真实、历史真实和客观真实。它要求报告文学所写的内容,所涉及的人和事等都是可以验证或不可被证伪的。在艺术和审美接受效果上看,报告文学带给读者的感受应该是客观、真实、准确、可信。

百年报告文学传统形塑了非虚构的价值追求
现代意义的报告文学大致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年出版),捷克记者基希的《秘密的中国》(1933年出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7年出版),墨西哥爱密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7年由包玉珂编译出版),捷克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1945年出版),这些作品常被视为现代报告文学的代表。
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创作的《戊戌政变记》,五四运动期间,冰心《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一批纪实作品,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的萌芽。而瞿秋白于1922年出版的《饿乡纪程》和稍晚些的《赤都心史》,周恩来的《旅欧通信》,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谢冰莹的《从军日记》,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1936年夏衍发表的《包身工》,宋之的发表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以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萧乾的《流民图》等,则被视为中国报告文学的早期典范。这些作品的作者,有许多都是记者,他们的作品最初也大多是在报纸上发表。因此,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最初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是以文艺通讯、战地通讯或特写、特稿的形式和名称出现的。
当然,一直以来都有人在宣扬报告文学中国古已有之论,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史书大多可被视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史记》是报告文学的雏形。这种观点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它实际上所要探究的是报告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渊源根脉。中国古代史书都追求不隐恶不讳善秉笔直书春秋笔法。这种非虚构的价值取向和写作方式与现代意义的报告文学在内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而从创作实践上看,报告文学的写作者也越来越追求历史学般的严谨客观准确真实,追求达致一种类似于史志、史记、史传、史录、史料文献式的长远价值。从这两方面考察,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着向史学靠拢和皈依的趋向。这,或许也是一种文学的返祖现象。从人文学科和人的认知、人的知识谱系等角度看,文史哲本是一家,文学和史学存在着同质性同根性同构性。这一点,在报告文学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往往既追求史的真实准确客观,也努力开掘哲理、哲思,期冀着能带给人们深刻的思考与启示。

非虚构是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
报告文学追求真实,要求具备非虚构特征。许多文学作品,无论是虚构文本或是非虚构文本,都追求达到一种逼真拟真、真实可感、令人信服的艺术效果,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有较好的代入感和共情体验,能够与作者笔下的人和事产生情感共鸣——这,实质上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真实或感受真实、接受真实,但是,报告文学所要求的真实性却并不止于此。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及真实性的价值追求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现代新闻业发展的产物,新闻性决定了报告文学的内容、素材,所涉及的人和事、现实和历史,都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凭空虚构、编造杜撰,这也正是报告文学所必须具备的真实性品格。但这种真实性并不简单等同于人物和事件的事实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真实、判断真实和本质真实,是在事实基础上进行历史考证、理性分析和本质评判,并予以艺术化了的真实。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根与本,基石和柱础,是报告文学的生命。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首先表现在所写内容、人物、事件和历史的可证性上。报告文学作者往往是通过倾听当事人的讲述、回忆,借助看或听当事人或知情者的日记、录像、录音、视频、微博、微信等资讯,采用田野调查的形式,运用多名“证人证言”、多种证据材料来反复印证、质证、校正和核实所采集内容的真实准确。这种工作类似于考古发掘和历史鉴证,也有点像法官的法理调查、证据质对(质证)。通过真人真事的互相印证、事实、文字记录、音视频资料、实物、遗迹、遗址、遗存等的相互比对,互证、验证、论证,共同确保报告文学所描写内容的确凿无误。
对于不可证性的内容,报告文学应尽量回避或干脆不写。因为这些内容必然带有虚构或虚假的成分。而这,则是违背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的。当然,历史无法完整复原,人们无法回到过去重返历史。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历史既具有可证性,同时又具有不可证性,任何形式的记忆、记录和书写,包括历史书写、历史叙事,甚至是现场直播、现场直录都必然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取舍性或某些缺陷。报告文学创作对于真实性品格的秉持和追求,实际上也只能是力求历史真实、判断真实、本质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内在结合与有机统一,只能是无限逼近历史本真和事实原貌。
非虚构的价值取向要求报告文学所描写的人、事、情、景等应该是必然的或或然的,而不能是否然的非然的。换言之,报告文学只能写那些证据确凿、真确、准确的内容,或者写那些可然性的、有可能的,合乎情、理、史、实,符合事理、情理,可以被认同、接受,能被读者认可为真实、可信的内容。举例来说,作家可以写一个会吸烟的人在某种特定场景中吸烟,因为这样的细节可能也可以发生,是可然性的、或然的。但是,对于否然的、不可能的内容,报告文学绝对不可凭空虚构或杜撰。亦即,那些在具体历史情境或场景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可信、不真切的内容,都是不能编造的,因为那些内容会被事实和史实证明为虚构和虚假,是伪事实或伪情节。例如,有篇作品写到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城市澡堂里的老百姓个个红光满面、身健体壮,——这个细节后来受到了人们的严厉指责,被认为是违背历史真实的“硬伤”。这位作家犯的错误就是描写了不然性的内容。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还体现在,所有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历史叙事,都是对已然——已成为过去及历史的事件、人物的描述与叙写。时间划分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切面。站在现在、今日、此时此刻的坐标原点,眺望昨日和已成前尘往事的过去,它们都已经或正在逐渐隐入历史深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就是“已然”。如果将时间长度进行高度浓缩,那么,任何历史都是当下史,都是当代史,都“刚刚”发生,“刚刚”过去;历史(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根本及基础,任何历史都是活的历史,都延续至今日乃至将来的生活中并将在其中不断“复活”或“重演”。报告文学所书写的,无论是新近发生的人和事,还是比较遥远的人和事,都是在记录历史,书写过去。这种历史叙事构成了报告文学史志性特征的基础。可以说,每篇报告文学作品都反映了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某些人群的社会生活生存现实和情感真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见证与历史存照,都具有不同的史志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这种史志价值的优长是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所难以匹敌的。
报告文学既然都是历史叙事,就必须遵循历史叙事的叙事伦理和基本准则,必须努力挖掘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力图恢复历史本貌和原貌,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等等。所有这些,也都是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所要求的。同时,我们亦应看到,报告文学毕竟不等同于历史叙事,它还应是文学叙事。它区别于其他历史叙事的地方,正在于它是以形象的方式再现历史和表现历史的,它总是寻求在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之间有机的融会结合,相互的渗透交融。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往往既是优秀的历史叙事,又是优秀的文学叙事。

报告文学既然应该同时是文学叙事,追求以形象的方式描写历史,那么,文学的基本元素报告文学也必须具备,特别是想象这一文学要素、文学特质。想象力是一项最基本的文学能力和艺术能力。想象力高低决定着艺术创造力的高下。失去想象,文学便会失去生命。报告文学坚持非虚构第一、真实性至上原则,反对并杜绝虚构编造,但绝不排斥亦不应排斥想象。恰恰相反,作为文学之一体裁,报告文学可以而且需要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学想象。合情合理的艺术想象并不等同于虚构,虚构是凭空想象臆造杜撰,是“无中生有”,而合情合理的艺术想象则是“有中生有”,是从真实的人物、事实出发,从史料史实出发,遵循事理、情理、法理、道理、伦理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等,进行合乎历史真实、本质真实、判断真实、艺术真实原则的揣摩、构思与塑造,这种想象给读者的阅读感受应该是可信的、真实的,同时还应该是艺术的、美的。譬如,何建明采写天津港大爆炸的《爆炸现场》,便很好地运用了主观想象,通过想象力图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消防队员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救火行动,有115名公安消防人员在爆炸中丧生或失踪。正如何建明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写现场最有说服力。他在写作报告文学时,首先高度重视对客观现场的采访、调查,注重对那些幸存下来的和逝去的生命的追溯,对生命背后故事的探究与探索。为了写好客观现场,何建明要求自己必须亲临爆炸现场。尽管爆炸现场经过清理,基本看不出原貌。但在爆炸炸出的那个大坑前,在清理过的废墟上,作者思绪飞扬,浮想联翩,他用自己的主观去充分地感受,接受心灵的洗涤与震荡,接受感动与悲恸的感染,凭借想象,抵达鲜活生动的主观现场。这是一个作家主体主动介入所要报告的真实事件及人物的过程。它激活了作家的创作灵感、动力和源泉。在痛切的回忆与想象中,他在努力搜索和寻找那一辆辆消防车,那一支支消防队和一个个消防队员。他们如同电影画面和镜头一样,在作家的脑海中一一浮现出来。那些谁也无法再次亲历、抵达或复原的惊心动魄的场景,被作家重新唤醒和唤回了。这便是作家的创造,通过主观介入与主体想象,重返历史现场和事件现场。当然,作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表现出客观现场和自己感受到的主观现场,而是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事件的本质,亦即何建明自己所言之“本质现场”。他不是简单直接地去描述那些公安消防英雄们是怎么牺牲的、牺牲得有多惨,牺牲后如何安葬等等,而是要写出消防队员们在生死瞬间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最宝贵的东西,表现人们为了拯救那些受伤的消防战士永不言弃的努力和永不停歇的大爱,又是如何为那些逝去的英魂奏响忧伤动人的安魂曲。《爆炸现场》既描写了事件现场,又呈现了生命现场,表现了生死场上公安消防战士们的情感现场。字里行间充溢着作家的情感和思考,这是一部作家情感与思想都时刻“在场”的“有我”写作,是一种主体主动介入的而非主观臆想的写作。何建明不止于表现惨烈现场,不是单纯描述灾难,而是采用观照现实、观照生活的手法,对灾难进行了全面考量,不是津津乐道于照相摄影式的反映或以惨烈血腥的展示为噱头吸引读者,而是力图超越灾难超越生死,思考何为生何为死如何生如何死,表现和彰显那些牺牲者和英雄身上最珍贵的品质与精神。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要求是多层次、多维度、综合的整体性真实,既须是历史真实、客观真实,又须是全部真实、总体真实。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做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这些重要论断同样适用于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亦须认真严肃地正确处理好“全部真实”与“局部真实”的关系。有人批评《中国农民调查》“失实”,其最主要的判断依据是,这部作品中所写的或许是中国部分农村(主要是安徽省)的局部真实,但并不适用于全部,更不宜冠以“中国”之名。梁鸿的《梁庄》或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所描述的或许也是当下中国农村部分或个别地方存在的状况,是部分“真实”,但未必或并不适用于全国、全部,如果将其当作中国当下农村整体性的真实写照或缩影,事实上是失之牵强的。要完整全面地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必须从宏观上、全局上深入了解和把握,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需要提取更多的农村样本及标本。
报告文学所要求的非虚构和真实性也是一种与当下相对的历史性的要求。这种真实性具有超越当下性,超越一时一地而具有历时性,长久性。在经过若干阶段时长之后反观回顾,报告文学所描述的内容仍旧是真实可信的,是真正的“信史”。换言之,报告文学的书写需要放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背景中,报告文学作家要有高远的历史站位,要从宏观上进行把握,而不是从当下的、眼前的现象和表象出发,描写皮毛的表面的内容,而需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揭示出本质性的真实、历史性的真实、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实。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又是一种客观真实。尽管在书写上可以运用想象,描述主观现场,借助主观揣摩还原历史,但是它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准确的、客观的,要能经得起不同的人群特别是当事人检阅验证,而不能仅凭主观臆断、想象推测。
总而言之,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或非虚构性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总体的、本质的真实,是逻辑判断真实、事实历史真实、想象真实、艺术真实的统一,是接受真实与客观真实的有机统一。
(本文系节选,全文完整版请阅《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第一期)
【作者简介】
李朝全,生于福建仙游,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学士,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理论专著《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非虚构文学论》《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长篇纪实《梦想照亮生活》《中国好人》《最好的时代》《国家书房》《少年英雄》《世纪知交:巴金与冰心》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人口文化奖。两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次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