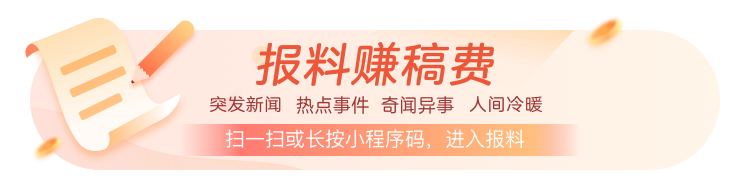没有母亲的母亲节,两位花甲老人这样做
今天是母亲节,朋友圈上各种云孝顺,盘点一圈下来,大多数的儿女对母亲表达感情的手段无外乎:送花、请吃饭、主动承揽家务。可是,有两位年过花甲的女儿,表达对母亲的爱和思念,却用了“写书”这么一种热烈而庄重的形式,其中一位还一写20年——在她60岁的时候动笔,直到80岁了才结集成书。(经出版社授权,文后附有两本书的独家书摘。)
失亲之痛不能分担,但生命的体验可以共鸣
4月27日是敬一丹的生日。敬一丹是观众熟知和喜爱的央视节目主持人,她主持的《焦点访谈》《感动中国》等多档有影响的节目,在屏幕内外与几代观众相伴。而在2019年4月27日,在敬一丹64岁生日这一天,她的妈妈却永远离开了人世。女儿的生日、妈妈的忌日,竟然是同一天。是巧合?是隐喻?敬一丹接受了这样的解释:64年前的这一天,我第一次脱离母体;64年后的这一天,我再一次脱离母体。

敬一丹(右)与母亲
妈妈在去世前两年被确诊为癌症。从确诊到去世,敬一丹一直陪伴在妈妈的病床边,那是她工作以后陪伴妈妈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她与妈妈慢慢告别的过程。这段时光伴随着病床边的焦虑和忧愁,伴随着病情起伏带来的困惑与纠结,同时也留下了妈妈与子女最后的温情。敬妈妈是一个刚强、有主见的职业女性,她是爱记录、喜欢留存和分享的人,她曾经用信件、文字、影像记录了自己和家庭的每一个历程。在病床上,妈妈对敬一丹说:“你把这一段写写吧!我不能写了。”敬一丹理解妈妈最后的心愿。寂静的夜里,她望着窗外的月亮,看着病床上的妈妈,一个书名在她的脑海里油然而生——“床前明月光”。从小熟悉的这五个字,在特定情景里有了新感觉,人们习惯用“夕阳”形容晚年,夕阳,意味着天将慢慢黑下来,但天黑了,还有月光。妈妈去世后,敬一丹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敬一丹回望妈妈的人生经历,倾诉至亲离别之痛,写出人生特定阶段的生命体验。可以说,写作,既是对妈妈的思念,也是对自己和亲人的疗愈。她说:失亲之痛不能分担,但生命的体验可以共鸣。
80岁老奶奶,写给妈妈的书
与敬一丹的名人身份不同,《秋园》的作者杨本芬却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之前从来没有写作经验的她,却在60岁的某一天,突然萌发了要把自己的妈妈——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女性一生写下来的念头。于是,在自家不足四平方米的厨房里,用两只高低不同的凳子权当书桌,在洗菜炖肉的间隙,杨本芬断断续续写下了对母亲秋园一生的故事。而这时杨本芬的老伴年事已高,有糖尿病和轻微的老年失忆症状,她必须像个护士一样伺候他。

杨本芬(右)与母亲。
在这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杨本芬断断续续写了20年,“写我母亲梁秋园一生的故事、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就注定会被深埋。 ”后来,儿童文学作家的女儿得知母亲在写作之后,帮她把这些故事发到“天涯”上,这些普通人的故事竟然也吸引来了很多粉丝。就在杨本芬老人80岁这一年,这本以其母亲名字命名的书《秋园》出版了。杨本芬出于好奇,最后把自己的书稿一称,重达八公斤!她说:“书写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 人到晚年,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赶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精彩书摘
《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

《床前明月光——为亲爱的妈妈送行》
暖,如同家人
妈妈端杯祝酒时,必定感谢刚子、淑荣对他们的照顾,还一再嘱咐我们,他们替你们当儿女的付出了辛苦,要感谢!
吃饭的时间到了,妈妈还躺在床上。
锅盖打开,蒸汽弥漫,淑荣在忙碌着。她帮助我爸妈做饭已经好几年了,特别了解老人的口味。笼屉里,馒头、花卷、豆包,还有南瓜掺面做成的淡黄色小兔子形状的面点。我情不自禁赞:“这么多种!”淑荣说:“就是想让奶奶多吃点儿,怎么也能吃一个吧!”
妈妈终于起来,她无力地坐在桌前,看着桌子上的饭菜,仍然提不起兴致,没有食欲。
我们都说:妈,看,淑荣做的小兔子多好,吃一个吧,你看看这个菜,都是你爱吃的。
妈妈拿起筷子,我们故作轻松却内心紧张地看着她,生怕她吞咽不畅呛到了。如果吃饭时第一口呛到了,接下来这顿饭就没有希望了。那些小兔子们琳琅满目摆在妈妈面前,妈妈只是看了看,却没有吃。
淑荣看着我妈妈憔悴的样子,转过身去,满脸写着失望,小声说:“白做了。”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她在心疼我的妈妈。
她就这样用心照顾着老人,千方百计地给我妈妈爸爸做好吃的,希望年迈的他们还能够吃得好,长力气。她熟悉妈妈的口味,二米饭、鲫鱼,还有乡村味道的菜叶包饭……后来又试探,蒸地瓜可以吃吧?酱炖土豆呢,可以吃吧?一样样试过。慢慢地,这些饭,我妈都不能吃了。
妈妈体重渐减,体力减弱。
后来妈妈不能经口进食了,做了胃瘘手术。淑荣就改成了做各种糊,磨各种浆,瓶瓶罐罐摆在面前,尽可能地在每一克食物里融进去多种营养,通过胃管注入妈妈体内。
妈妈做了手术以后,她立刻变成了护工。医生在床前教家人做胃瘘手术后伤口的护理,淑荣认真地学,接下来,她每天做护理,越做越熟练了。
妈妈身上的各种管子越来越多,淑荣也变得越来越专业了。她熟悉每一个管子的功能,知道每一个管子应该什么时候进行怎样的操作。她操作的时候,护士长看到了,说:你现在都可以培训护工了。
妈妈长时间卧床,淑荣每天都在为妈妈清洁,从头到脚没有一点马虎。床前,灯下,她心到眼到手到,就像照料一个婴儿一样,照料着病重的老人。经常是,我没有想到的细节,淑荣却想到了,做到了。她给了我妈妈亲人般的呵护。
我妈妈有几十年的吸烟史。她病后说:“我要是不再抽烟,就是我不行了。”果然,妈妈的病越来越重,烟也抽得越来越少了,甚至,她无力的手已经拿不住烟了。淑荣总能看出我妈想抽烟了,很多次,我看到,淑荣点着烟,轻轻放在我妈的唇边。平时,我那么希望妈妈少抽烟,不抽烟,这时,我却想,幸好淑荣能想到,就让妈妈满足一下吧。
妈妈病重听不见的时候,淑荣很懂妈妈的需求,后来,在更需要沟通的时候,淑荣就只能写小纸条。
淑荣很小的时候,家里日子困难,就辍学了,在农村老家辛苦生活,没能有机会再进学校。她说,写纸条,有的字写不上来,就在手机上查,再写出来。
她写道:
奶奶,我给你打个通便药,你在床上忍一会儿,就能便出来。要是你不忍,就白打了。你不大便,我很害怕。堵了肠子不便出来,太危险了。你别急着下床便,你就在床上便,我能收拾。
看到淑荣的纸条,我泪流满面。
她是真着急,真心疼,真负责。在床边,点点滴滴善良的付出,她给了奶奶安全感。
我妈妈曾经说,她又多了一个孙女儿,而这个孙女是在她晚年最需要的时候来到她身边的。妈妈在最后的日子,有些细节的叮嘱是对淑荣说的。她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不要害怕,我的头发要给我往后梳,别忘了,要把发卡摘下来。”
我妈病越来越重了,家人全力以赴,在病房,在床前。
老爸呢?爸爸在家里,贴身照顾爸爸的是刚子。刚子是我老爸前几年因骨折住院时请来的护工,后来从医院到了我家,专门照顾老爸。
我爸爸骨折痊愈了,但小脑萎缩,记忆力在退化,生活能力在减弱。刚子是在老人渐渐失能的过程中来到老人身边的,我老爸叫不出他的名字,却知道他是可以依赖,可以信任的。刚子能细微地察觉我老爸的情绪起伏、身体变化。他会告诉我们:爷爷这两天有点儿糊涂,爷爷有点儿蔫儿,爷爷愿意去海边看热闹,爷爷好像在想心事……那种体贴,就像对自家老人,他成为让全家人信任和放心的人。
刚子和老两口相处,自在温暖。我经常听到他们在聊天,从农村到城里,从天南到海北,从爹妈到儿女,从人情世故到家长里短……刚子和我妈妈成了忘年交。
在饭桌上,我妈的习惯是,夹菜让菜,不会让儿女,会让儿媳女婿,最让的是刚子和淑荣。逢年过节,我妈在饭桌上总会这样:
“刚子,吃这个。再盛点儿!”
“你咋不吃呢,淑荣?减什么肥!”
说着,我妈就用自己的筷子,夹了肉,夹了鸡腿,直接放在他们的碗里。
我说:“妈,别用你的筷子给人家夹菜啊!”
我妈说:“嗨呀,也不是外人!”
妈妈端杯祝酒时,必定感谢刚子、淑荣对他们的照顾,还一再嘱咐我们,他们替你们当儿女的付出了辛苦,要感谢!
我妈多次说,刚子是给老人晚年带来了安全感的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老妈在想后事了,她最放心不下的是我老爸。我妈和刚子拉钩相约,希望刚子能够好好地照料爷爷,伴他到最后。
我妈妈走了以后,我在妈妈的微信里看到她和刚子的对话,刚子说:我家从山东闯关东到了东北,我从小没有在爷爷奶奶跟前生活过,而认识了你们, 我又有爷爷奶奶了。
阳台上,有几个大花盆,妈妈曾在那里种苦菊;
围墙边,有一小块空地,我妈妈曾在那里种地瓜。
我妈不在了,淑荣又种了苦菊,刚子又栽上了地瓜秧。如今,那里,绿油油透着生机。
《秋园》

《秋园》
妈妈的童年,在十二岁那年春天结束了
秋园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来得很是蹊跷。前两日还需穿棉袍夹袄,隔天气温就升至二三十度,太阳底下恨不得着单褂了。天井里的一丛迎春,仿佛不经蓓蕾孕育就直接爆出花朵。葆和药店门前那株垂柳,数月来干枯失色,却似乎一夜之间便抽出细嫩叶芽,阳光照耀下如淡绿的碎金,在早来的春风里无知无觉地飘荡。
那日梁先生诊完一个病人,踱进内室,手里举着两张票子,一脸高兴的神气,对女眷们说:
“刚才来看病的客人在市政厅做官,送了两张游园会的票子答谢我,我看就让清婉和清扬去吧。”
清婉是大嫂,清扬是二嫂。这两个名字是她们嫁进梁家后,梁先生替她们起的。
此次游园会在报上张扬有些时日了,请的都是城中官员、名流或富绅的女眷。这种事在这个保守的古城算是首次。药店虽说生意不错,可说到底梁先生也不过是个郎中,按理说是拿不到票子的。此次意外得票两张,他不由满心欢喜。
二嫂清扬还是小孩心性,活泼爱玩。平日里她除了缝缝绣绣,就是帮着切药、晾药、配药,除了家里那几个人,谁都见不到,闷都闷死了。她马上笑嘻嘻地站起身,从家公手中接过票。
大嫂清婉担心自己那双小脚,神色间不免有些扭捏。清扬马上说:“姐姐,这整个洛阳城,还能找得出几双我这样的大脚?去游园的太太小姐,怕不都是小脚⋯⋯”大嫂立刻被说服了。
游园会那天一大早,清婉、清扬就起来打扮:脸上胭脂水粉一样不缺,身上套着自己最好的织锦缎夹袍,高高的立领把脖子撑得长长的。袍子的腰身特别紧窄,二嫂有点胖,边穿边吸气,嘴里直叫“哎哟”。秋园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她们,羡慕了一番她们的漂亮衣裳,就照常上学去了。
下午三点从学堂回家的路上,秋园感觉城里有点奇怪。店堂里的人都从店里出来了,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口议论纷纷。路上行人神色间自带一番仓皇,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
秋园回到家,发现葆和药店那两扇朱红大门大白天破天荒地紧闭着。门前围着一堆人,隔壁金店的掌柜也不做生意了,布店的掌柜也跑出来了。看见秋园,他们都转过身来。
“船沉了。”在一张张翕动的嘴里,秋园听明白了这三个字。
洛河里那条画舫游船几乎是在一眨眼间沉没的。那些小姐太太拥挤在一处,在人们反应过来之前,游船迅速失衡,一头扎进水中,飞快地消失了。清婉和清扬都在那艘船上。她们裹着她们的织锦缎窄袍,丧生在洛河里面。
办完两位儿媳的丧事,梁先生就病倒了。身体受了早春的风寒,邪毒入侵。身病加心病,终至一病不起,不过短短半个月就病故了。可怜梁先生一生干的都是悬壶济世的事,却没料到自己会英年早逝。
梁先生缠绵病榻的半月间,一直是秋园的大哥秋成陪床。他在父亲身侧搭了个小榻,衣不解带地伺候。办完父亲的丧事,秋成便得了怪病 — 全身乏力,颤抖个不停。病名无从查考,病因倒可想而知:半个多月里,失妻丧父,连办三场丧事,这年轻人撑不住了。
秋园的童年时代结束于十二岁——那年春天,她失去了三位亲人。
亲手送走自己的亲人,这只是开头。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秋园生下五个孩子,带活三个,夭折两个。四十六岁,她埋葬了丈夫。秋园自己活到了八十九岁。去世前那几年,她常说的话是:“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
【记者】陈小庚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