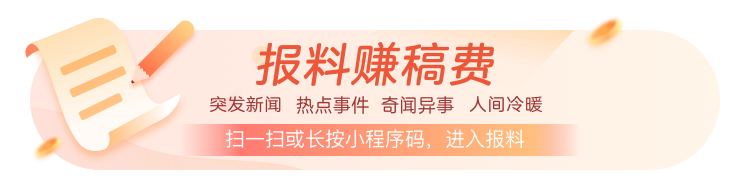寻幽不惮远 乃至归猿洞——去清远峡山窥探归猿文化的魅力
“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
一头猿猴误入人间,化形为人与心上人相爱、成家、生子,却依旧向往着啸傲山林的自由自在。
对于以齐天大圣为代表,有关的猿猴传奇故事,你一定早已耳熟能详。但你是否知道,在清远的峡山,也有一个流传近千年,讲述爱情、自由、返归天性与自然的“峡山归猿”的故事呢?
 清远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清同治元年伍常勋(紫游)献环图轴》(市博物馆提供)
清远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清同治元年伍常勋(紫游)献环图轴》(市博物馆提供)
01
源起
归猿故事
或许你可以选个时间,逃离现代都市生活的羁旅形役,远离喧嚣的市区,从白庙渔村乘船入峡山,沿着险峻难辨的山路寻找归猿洞,追寻在这片山水之中流传千年的“峡山归辕”的传奇故事。
今天的清远峡山森林茂密,鸟兽众多,在古代更有大量的猿猴繁衍其中。唐代诗人李翱在诗文中说,峡山猿猴成群结队(“鱼龙睛向戏,猿穴晓成群”《题峡山》)。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清朝初年,从峡山到英德一带的山峰上,仍有成群结队的猿猴啸聚其中,哀鸣之声连绵不断(“群猿聚其间,声声相应,侧侧凄凄”《广东新语》)。
在峡山流传的众多民间故事中,发生在猿猴所化的女子与书生孙恪之间的“峡山归猿”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盛唐之时,峡山寺庙中的小沙弥慧幽养了一只聪明可爱的小猿猴,天子使者高力士喜欢小猿猴聪慧,将其带到京都长安,献给了唐明皇。“安史之乱”时,天下大乱,猿猴逃出宫中,化为女子,以袁为姓。到了广德年间,考科举落榜的书生孙恪对她一见倾心,两人结为夫妻,度过了一段恩爱情深的日子。
袁氏女子容貌明艳,举止端庄,处事从容,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却并非柔弱可欺。面对被表哥劝说,携带宝剑意图威慑妖物的孙恪时,袁氏不谈人妖之别,却从恩义、节操立论,痛斥孙恪不顾夫妻恩情,恩将仇报,她将宝剑折断成一截截的碎片,却原谅了孙恪,还以两人在一起多年孙恪仍平安无事表明自己的真心。
后来,孙恪携全家到南康州任经略判官,南下经过峡山中寺庙时,袁氏触景生情,归还当年离开时戴在脖子上的碧玉环,题诗留念,变回猿猴的形态,逐伴归山,攀援而去,隐于山林之中。
猿女与孙恪的归猿故事最早出现在唐朝晚期裴铏的《传奇》中的《孙恪传》中(宋《太平广记》收录),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晚唐作家顾夐也有《袁氏传》之创作;在飞来寺内,还曾经竖有(宋)刘义庆《归猿洞》碑记和(元)杨观重刻石碑,都记述了这个传奇故事。
 清远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清同治元年伍常勋(紫游)献环图轴》局部。(市博物馆提供)
清远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清同治元年伍常勋(紫游)献环图轴》局部。(市博物馆提供)
02
生发
归猿文化或自苏轼开始
“峡山归猿”这一故事最早出现在裴铏《孙恪传》中时,发生地却并非清远。但奇妙的是,千年以来,这一故事却在清远生根开花。
回溯历史,最早在诗文中将这一故事与清远峡山连在一起的,是与清远颇有缘分的大文豪苏轼。
公元1094年(宋邵圣元年),贬官南下的苏轼从定州(今属河北)出发,于当年九月初经江西越大庾岭进入岭南,九月十三日,苏轼到达峡山飞来寺。在这里,苏轼泊舟山下,登上半山中的飞来寺游览。
峡山一江两岸风景秀丽,苏轼在此赋诗一首,起首“天开清远峡 地转凝碧湾”两句,历代广为流传。诗中最后六句“佳人剑翁孙,游戏暂人间。忽忆啸云侣,赋诗留玉环。林深不可见,雾雨霾鬐鬟”,引用了归猿的故事典故,用诗句将猿女的故事重新述说,写出雨雾缭绕,树木幽深,不见猿女踪影的伤感寂寥之意。
比这六句诗更加直接的,是苏轼在诗自注中说道,《孙恪传》中记载的袁氏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传奇所记孙恪妻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见猿者”)
在裴铏写作《孙恪传》的数百年后,苏轼的到来让归猿故事被迁移到了清远。归猿故事在清远生根开花,即从苏轼开始。
这一论点,从古至今多有学者支持,在清远本地,潘煜池等研究者也曾撰文论述。
峡山有着适合归猿故事生长的土壤,故事中蕴含着“出世”、回归自然的观念,得到了峡山一代文化土壤的滋养,在清远进一步发展。此后,峡山相继出现了归猿洞、归猿峰、问归亭、金锁潭等一系列“归猿系列”景点和大量的诗歌、戏剧。历代诗人墨客游历峡山时,往往为归猿故事所感,写诗赋文纪念一番。
清同治元年(1862),飞来寺住持僧鼎中(号本净)邀请伍常勋,根据流传千年的归猿故事作画一幅。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在清远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见到这幅《清同治伍常勋献环图轴》。
画中,山石磊落,烟雾缭绕,苍松枝叶秀拔,蟠桃硕果累累。在松荫下有两只白猿:一白猿躬身戏物,另一白猿回首张望,似在呼唤着同伴。画幅中央有三个人物:仕女双膝下跪,手捧玉环献上;男童躬身俯首,伸手代取玉环;长老坐于石台,手执佛尘,神态安详自若。长老背后,放着经典诗书和插有万年青的花瓶。
 清远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清同治元年伍常勋(紫游)献环图轴》局部。(市博物馆提供)
清远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清同治元年伍常勋(紫游)献环图轴》局部。(市博物馆提供)
03
繁盛
归猿文化千载不息
寻幽不惮远,乃至归猿洞。
细石路盘行,霜林日气烘。
阴风出土口,飒飒添寒冻。
下临万丈溪,圆窍如攲瓮。
淄珠结紫金,石壁巢金凤。
顾此生遐想,乾坤何巧弄?
这是清代诗人张鲲的《归猿洞诗》诗句,描写的是峡山归猿洞如入画图的风貌。
归猿洞何时出现,目前查不到确切记载。明清之际,已有关于“归猿洞”的词、赋或诗文传世,明代朱士赞的《归猿洞诗》对传奇怪异颇有猜疑,他写道“逐队归山去,玉环遗此山;千秋传异事,吾意有无间。
归猿“异事”虽不可尽信,但“归猿洞”确实存在。张鲲的诗具体地描述了归猿洞的风貌,作者很有可能曾亲临实地。清初《禺峡山志》记载:“归猿洞在古寺后仙猿峰之陡绝处,中隔悬崖,通以梁,游者多惊怪,不敢渡,过此则洞壑幽深,树木岑郁,真仙境也”。清代编修的《清远县志》,也已有“归猿洞”的条目。
经过峡山的文人墨客中,很多人听到归猿故事后心有所感。在苏轼之后,宋代诗人胡铨、张以宁、崔舆之、元代诗人贾燠、张子寿,明代朱士赞、明末清初王夫之、清代王士贞、朱奉尊、屈大钧等,都曾以归猿故事典故入诗。
“犹恐孙郎妒,相邀弄夕阳”(明末清初 王夫之)“飞来古寺是耶非,何处归猿向此归”(清屈大钧)等,是他们见景怀古,心有所感。
“猿吟峡僧定”(明汤显祖),“逐伴归山去,持环扣寺还。”(明朱士赞),“猿狝有时闻”(清廖明良),“澄潭西去沉金锁,古洞猿归带玉环”(清朱彝尊),是他们有感于归猿故事中的“归去”“出世”。
“一声长啸入烟萝,碧玉遗环断爱河”“玉环春梦未分明,不是孙郎亦怆情”“猿挥孙恪千年泪,月照维摩半夜禅”,是他们对人间美好姻缘破灭的同情和惋惜。
归猿故事早已被编入戏剧。元代剧作家郑廷玉写有杂剧《孙恪遇猿》。相传,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为了写作《牡丹亭》,专程到飞来寺做了一名挂名道士,别号“清远道人”。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牡丹亭》剧情与归猿传说颇多相似之处。在现代,归猿故事也被多次改编成粤剧。如潘康莹的《禺峡奇缘》、李锦洪的《归猿记》和何必的《风雨归猿》。
此外,归猿故事还被制成美术作品。20世纪80年代,广州岭南出版社出版的广东风物传说连环画系列,其中就有一部以清远峡山归猿故事为内容的连环画。
“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在《孙恪传》中出自袁氏的吟诵,是保持天性、回归自然,摆脱现实社会羁绊和俗世人情束缚,获得自由人生的向往与追求,今天读起来仍有着独特的魅力。
 4月25日,归猿洞外石刻需仔细辨认。
4月25日,归猿洞外石刻需仔细辨认。
 4月25日,归猿洞前有近十米高的沟壑,洞口被树木遮挡,难以见其全貌。
4月25日,归猿洞前有近十米高的沟壑,洞口被树木遮挡,难以见其全貌。
采写:毛远策
摄影:李思靖
资料提供:清远市博物馆、清远市艺术研究室
责编:叶紫
校对:喵果果
编审:刘厚斌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