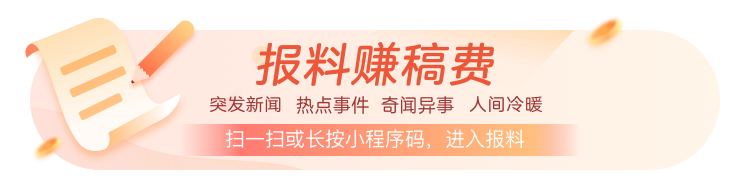知识付费下半场,重演知识焦虑还是开启新知?

热门视频社交平台以新姿态入局知识付费,对“二手知识”“碎片化”“贩卖焦虑”的质疑会重演吗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11期
文 |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林澜 梁文雪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7320,细读大约需要15分钟
早晨6点半。中午12点。深夜11点。凌晨2点。
无论你在哪个时间打开B站(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搜索“直播自习”,永远有正在直播的自习室。点进。背景音有时是白噪音、有时是轻音乐,直播屏幕上没有人脸,通常是收拾整齐的书桌,日历、电脑、参考书或作业本,有时侧栏列出直播主的学习计划或目标,最多露出一双正在划笔记或翻书敲键盘的手。
屏幕上唯一变化的是桌上的时钟或计时器。数字的跳动提醒着刚进直播间的观众,这不是一个静止的录播屏幕,以及——时间在流逝,你该学习了。
“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在B站学习!”
B站用户们在弹幕和评论区这样感慨。近两年,不仅是直播自习,各专业领域都涌现了许多科普类原创视频。随着各种名师课程视频被用户自主剪辑搬运到B站、抖音等平台,许多大学校园的专业老师因此走红:
靠着“法外狂徒张三”的刑法案例故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B站火了,入驻B站的第一条问候视频,飞驰而过的弹幕里,齐刷刷一列“老师好”;北师大物理系老教授赵峥在B站讲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黑洞等科普内容的付费课程宣导视频,播放量两百多万;在抖音,操着一口流利的湖北麻城普通话,讲古代诗词的老教授戴建业老师也“火得一塌糊涂”,随便一条短视频点赞就是两千多万,抖音和今日头条粉丝如今已达500万……
在用户自发行为的带动下,这些以娱乐或青年亚文化起家的视频社交平台,悄然进军知识付费的下半场。类似“知识分享官”的活动,在不少自制原创视频网站出现,同时,知识“大V”们也纷纷被邀请入驻,为平台量身定做知识与技能付费课程。
2016年前后,知识付费的概念一度席卷市场,如“得到”、“喜马拉雅”、“樊登读书”等等,同时遭到各种质疑:“贩卖知识焦虑”,“被咀嚼过一遍的‘二手知识’不能替代读书学习”,“知识的碎片化大行其道”……
这次,知识付费下半场还会重演类似的尴尬吗?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戴建业成为抖音网红后,出版机构争相出版他的作品 图/受访者提供
老教授成“抖音网红”
两年前,偶然从年轻同事口中得知自己成了“抖音网红”的戴建业吓了一大跳。
彼时,年过花甲的中文系教授戴建业根本不知道“抖音”是什么。可视频是谁传上去的?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
十年前,超星公司策划了一档“超星名师讲坛”栏目,调查全国名师并进大学课堂为他们录像。在华中师范大学颇受欢迎的中文系教授戴建业也受邀录了一门课程,叫“走近大诗人”,内容主要是讲授李白、杜甫、陶渊明三位大诗人。
古代文学星河璀璨,戴建业本来想一直讲下去,后因教学改革,这门课未能延续,他渐渐将这件事放下。不过,超星给他录下的这门课,在各大学一直深受欢迎。直到2018年前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逐渐占领市场,超星公司便趁势将之前录制的名师讲坛视频稍加剪辑,截取有趣、有料的短片段,发布到其抖音账号上。
当时,除戴建业外,钱理群、王蒙、易中天、白岩松、俞敏洪等不少名人名师的短视频也被超星挂了上去,但激起的水波不大,文学界大咖如钱理群、王蒙,发布前几天的播放量也不过几千。直到戴建业的短视频发布第一天,播放量破两千万,点赞上百万,评论区也非常活跃。
但戴建业对抖音上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大概半年后,教研室的一位青年老师告诉他,他“在抖音上红得一塌糊涂”。
戴建业听了感到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什么叫‘抖音’。”
年轻同事说,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App,在手机上看。
戴建业还是一脸茫然,下载个什么?怎么看?他对手机的新鲜玩意向来不太精通,又好奇,“小子你过来给我搞(抖音)。”
那是戴建业第一次看到抖音上的自己。点赞量最高的视频里,戴建业讲的内容是这样的:“李白的自我感觉之好,好到你感到恐怖。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他搞不定,而且他老人家更搞笑的是,他一直相信自己身上有仙气……”
“爆款哦,”他如今学会了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搞笑吗?他倒没觉得多好笑,如今大家眼里的“幽默机智”,在他小时候被父亲教训称说话没正经、轻佻,因此挨打也是常有的事。只是意外,自己因为普通话蹩脚被嘲笑了大半辈子,“哪里想得到大家竟然喜欢我的普通话?”
曾经在博客时代就是“网易十大文化历史类博主”的他,平时就有写作杂文随笔的习惯。很快,他写了篇很长的文章,分析娱乐产品内诞生教育知识类爆款的时代背景和原因,一时间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转载,也引来字节跳动公司主动递上橄榄枝,签约戴建业开通个人头条号、抖音号。
但与素人网红相比,戴建业不用操心太多运营之类的事务。他不会剪视频,于是把抖音视频号的发布和运营交给了有过合作的果麦文化传媒公司;他不怕模仿和抄袭,“说话方式是努力不到的”,更别提他有大半辈子的古代文学储备作底;也没有人要求他迎合平台风格,“我是一个很大的大V嘛”,他自然地说着“大V”这样的词,“我是这么一个人,就表现出这个样子,很多人就喜欢了。”

高考模拟考场视频的弹幕
入局知识付费,新兴平台登场
在抖音、B站这类用户基数大、用户自发创作的视频平台,像戴建业一样从专业领域涌现的“知识网红”还有很多,遍及人文、社科、艺术、科学各领域。无论是面向平台专门创作的原创科普博主,还是课堂偶然被搬运到网站上的老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在专业领域内有多年的知识积累,并乐于以通俗风趣的方式向普通大众分享。
比起“知识网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敏更愿意称他们为有声誉的信息“把关人”。在传播学里,“把关人(gatekeeper)”这个概念指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的传播者。她认为,当下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一方面造成了信息过剩,且错综复杂、真假难辨;但同时,“公众有越来越大的知识需求,这种需求包含了对合格信息的渴望,观点的解读、碰撞,对过往真知灼见的共享。”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有专业能力的人帮助我们剔除无用信息,理清思路,总结概括,分享传播,甚至把这些信息梳理成比较系统的知识或经验,那么无论是市场和公众都欢迎有声誉的信息‘把关人’。”
周敏认为这是目前这个市场比较红火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而未必出于“知识焦虑”或“知识恐慌”——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也是背后的驱动力之一。
事实上,反观知识付费下半场入局的平台如B站,与其说是平台主动谋求布局知识付费,不如说是顺势而为——最初引发热度的知识类视频或直播学习行为,基本是用户自发,达到一定量级后才由平台出面“正规收编”。
约两年前,B站的前端和后台数据已经显示出“在B站学习”的潜力。2018年有1827万人在B站学习,相当于2018年高考人数的两倍。2019年,伴着Vlog热潮的兴起,B站学习类UP主数量同比增长151%,学习视频播放量也同比增长274%,泛知识学习类内容的观看用户数则突破5000万,相当于2019年高考人数的五倍。
根据用户画像,B站用户集中于15岁到24岁这个年龄层,70%以上是中小学及大学的学生群体,本身正处于学习期或广泛涉猎知识、具备好奇心的阶段。在内容生产方面,B站也早已不是最初那个只有二次元、ACG(动画、漫画、游戏)的亚文化网站。关于知识和经验分享,甚至在官方发起“知识分享官”这类激励活动之前,B站上关于科普、人文等各种领域的泛知识内容生态已非常完整,诸如“我在B站学习”的用户玩笑也被官方认可并“活学活用”,甚至出现在央视、《人民日报》等媒体上。
某种程度上,这为平台后续推出专门的学习区、“知识分享官”激励活动、付费课程定下了市场风向。2019年初,B站决定组建付费内容制作团队,并在十个月后面向站内上线了第一款付费课程《15节课轻松学Pr剪辑》,副标题则拟为非常具备B站实用特色的文案“Vlog、混剪、鬼畜、特效全搞定”。
尽管仍在站内内测阶段、尚未站外推广,但上线半年,这门需要花费99元购买的课程,销量已接近五万份。此后,他们陆续推出AE、PS、动漫奇妙艺术、日语入门学习、宇宙学等付费课程,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目前的销量感到满意。相较于其他视频或知识付费平台,1.4亿的用户月活、高黏性的青年社区文化是B站引以为傲的用户基础,其制作的付费内容也与其他知识付费平台有较大差异化,短期内将把付费内容发布权限集中在官方,并非向所有Up主(即在B站发布视频的博主)开放。
“现在行业整体处于中晚期。”B站付费内容团队的制作人蔡草草(化名)在知识付费行业工作了五年。他认为当下的知识付费市场处于“下半场”:“得到、喜马拉雅主打30岁以上人群,但24岁以下的用户不到20%。15到24岁人群可以说是知识付费的新生地。”
相较之下,以短视频为主流的平台如抖音、快手,在知识产品的定制方面更趋“去中心化”。抖音官方也推出过知识分享官活动,但基于媒介特性和用户群体的特征、使用习惯,入驻抖音的在线教育产品通常以短视频或直播带购买链接的形式运作,比如不少业务主营中小学线上教育的公司会为旗下各学科老师注册抖音号,签约老师以短视频形式分享教学课堂片段,或面向家长分享教育方法,随带的购买链接里便是相关的全套系列课程,抖音从中获得平台分成。以这个路径发生的购买行为,底层逻辑其实与购买实物商品无异,但也是将变现潜力最大可能地赋予用户。
知识分享和学习行为从未停止过,周敏觉得,古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只不过如今,传播介质从书本、面授等传统方式扩大到了网络等新科技平台,但知识传播的主体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大多依旧是学者、教师、学生、某领域专家,或称为“分享型知识分子”——“他们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敏 图/受访者提供
在B站,一门宇宙学课程的诞生
在大众化的平台上,“泛知识”分享多在司空见惯的领域,如教育、职场、生活类的实用知识、技能和经验。在一个面向年轻群体的平台,大学物理系教授正经开课科普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黑洞,依旧是一件新鲜事。
和戴建业类似,生于1943年的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峥,在去年之前也不知“B站”为何物。但B站有用户认识他——赵峥在北师大的广义相对论基础全116讲超星课堂视频,以及近现代物理学漫步系列讲座的网易公开课视频,在B站的播放量总计超15万。
与此同时,B站的付费内容团队也关注到了他。去年加入该团队的蔡草草回忆,在梳理内容地图时,他们发现硬核科技、科幻类的选题在B站的用户关注度高,这其中也包括对宇宙学的兴趣,便动念产出宇宙学相关的付费课程,希望能找到专业领域内的头部老师合作。
但在策划之初,对于合作学者的类型,团队其实有些犹豫:是找专业研究非常深入扎实、但可能表达相对枯燥的研究型学者,还是找表达非常吸引人、注重基础科普的大众化学者?他们担心的是,过于专业和高阶的课程内容恐怕不利于用户理解和买单,但另一方面,他们主观上希望打破知识付费曾受到的质疑,比如知识的碎片化、娱乐化等问题。
“但非常幸运,赵峥老师两个特点都具备。他既是国内物理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同时讲述感又非常好。”蔡草草说。
赵峥在北师大的课程向来受欢迎,他喜欢在讲述物理概念的间隙,穿插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霍金、牛顿等人的生平轶事,或是名人们充满失败与艰辛的研究过程,常惹得学生们笑声不断。他最喜欢举的例子之一是关于神童与非神童的比较:“托马斯·杨是神童,对很多领域都有贡献,但牛顿、爱因斯坦都不是神童。可见神童不神童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既要关注那些很优秀的同学,也要关注那些成绩一般的同学。”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彼时年轻的赵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读本科。当时的中科大非常注重名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比如数学系是华罗庚等老师上课。而在赵峥所在的物理系,理论力学、电学、热学、光学这类基础课,上课的老师是严济慈、钱临照等老院士。“文革”结束后,本已中断自然科学研究六七年的赵峥报考北师大天文系研究生,在刘辽教授门下研究黑洞、相对论,成为国内最早一批接触和研究相对论的学者;博士阶段则师从诺尔贝奖得主普利高津,198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如今,赵峥已年过古稀。随着年岁渐长,他渐渐确认一个观点:科学家最重要的成就多是在年轻时期做出的,年长者创新能力逐渐降低,却有更深广的知识储备。
现在,科普的任务轮到他们头上了。
早在几年前,赵峥与“读书人”团队便有合作,会录制一些10分钟左右的短视频,推荐科普书籍。他也做过不少面向非物理专业学生的科普讲座,从在北师大开设的北京高校通识选修课,到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的系列讲座等等。他习惯在上课时观察学生的表情和反应:什么时候学生注意力开始涣散,什么时候眼神显得很迷茫,什么时候开始困了,甚或有人离场……
根据反应,赵峥会及时调整自己的讲课内容,比如适时插入轻松的故事,又比如解释得更详细,或思考学生可能为什么离开,再据此调整讲座的内容、讲述顺序。多次科普讲座下来,他发现,课堂不必严格按时间顺序讲起,比起学生相对熟悉的伽利略、牛顿,从爱因斯坦、霍金的发现讲起总是更容易抓住学生的兴趣。而用这种方式先勾起好奇和兴趣、再回溯历史,学生们竟也能听进去曾经觉得枯燥的内容。
2019年,B站抱着为赵峥打造付费课程的想法找到读书人团队合作。在赵峥的书房里,读书人团队曾为他录制过科普相关内容,主题也围绕赵峥常在大学分享的通识讲座“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足有四大段、长达十个多小时。以这些素材为基础,作为内容监制的B站对读书人团队提出了一系列视频打磨要求,以符合B站平台的审美调性和观看习惯。
读书人团队原以为,当下是短视频为主流的快时代,年轻人应该也喜欢看短视频,于是最初提出了每集3到10分钟的大纲构想,一集一个知识点——但B站的修改要求却出乎他们意料。实际上,B站的数据显示,在这个长视频社区,只要是内容足够优秀的作品,观看时长和页面停留时间非常长,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年轻用户对优质内容显示出了足够的耐心。
B站要求读书人团队注重单集主题的完整性,单集时长则可以放宽到20-30分钟,后期样片制作过程中,在许多技术形式层面做了很多符合用户审美习惯的调整。但在赵峥的课程内容方面,考虑到科学知识的严谨性和保持老师个人风格,除了口误外几乎不用特意重录。
2020年1月底,赵峥在B站的宇宙学付费课程正式上线,封面图赫然入眼的文案是——“你对宇宙的力量一无所知。”
这门定价39元的课程与B站其他课程相比不算贵,考虑到占用户70%的学生群体的消费能力,B站最初的想法是走低价策略。上线至今不到两个月,这一“不实用”的冷门课程销量近一万份。
故事的另一边,由于原视频素材版权归读书人团队所有,赵峥没有太被卷入这门知识付费的生意里。在接受采访之前,赵峥对B站依然了解不多,他没有看过自己的B站视频,不知道“弹幕”是什么,正如他也不曾看过网易公开课或超星课程里的自己——不回看自己的影像,这仅仅是他的习惯。
但在听到关于“弹幕”的解释后,他呵呵笑了:“还蛮好玩的嘛。”
“如果人们从你的科普视频里,只记住了逸闻趣事,没弄懂相对论呢?”采访时我曾问。
“那也没关系。只要引起你对科学的兴趣,产生一点好奇,也是达到目的了。也可能有的人就此入门,他们会主动去找更多的资料系统学习、钻研。”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峥在北师大讲台上的留影 图/受访者提供
他们也曾是学习者
赵峥感慨的是,五六十年过去,曾经人们是一书难求,而如今网络的发展几乎让知识唾手可得,但真正愿意下苦工夫吃透知识的学习者,在每个年代都同样稀有。
赵峥最早对广义相对论产生兴趣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期间,那时,全中国也没有几个懂广义相对论的人。1965年暑假前,他偶然在学校附近买到一本讲授广义相对论的小册子,意大利人坦盖利尼著、朱培豫翻译的《广义相对论导论》,以这本篇幅短小的《广义相对论导论》为主,辅以爱因斯坦艰深的原著《相对论的意义》和博格曼厚重的《相对论引论》,他苦钻了一整个暑假,每天上午学习四小时,无奈实在太难,他依旧半懂半不懂,却无人可问。
而他的研究生导师刘辽,是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剥夺教职并指派到图书馆当管理员期间,在斗争的闲暇偷偷看书钻研相对论和粒子物理,改革开放后才有机会出来宣讲广义相对论,与方励之等人一起成为当时中国大陆主要讲授广义相对论并开展相关科研的学者。
如今,轻松点点鼠标、敲击键盘就能看到全球名校名师课堂的人们,拥有着他们当年羡慕不及的资源、条件,却也面对着新的信息选择、时间精力管理困境。
老一辈的人也不能全然免于其困。比如,成名自然给戴建业带来许多看得见的好处,多家出版机构争相抢夺他的作品版权,也有不少机构找来,想与他合作录制视频或音频课程。“时下人们常常嘲笑说,教授们的专著只有两个读者——责编和作者。我的学术著作竟然能成为畅销书,已让我大感意外。”在九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他在序言里这样写。
然而苦恼的是,戴建业近两年不得不把时间浪费在许多社会应酬事务上。他迫切地希望几年后彻底结束这种局面,回到书斋静心读书做学问:
“一个人不能永远处在聚光灯下,长期很痛苦,不能冷静,这会毁了他。我红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成为“抖音网红”的短暂快乐,对戴建业来说永远比不上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文章或著作的成就感。但戴建业也开始转变观念,他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而“短视频是视频中的绝句”。他乐观地相信,一定会有经典短视频流传下来。
尽管社会事务多了不少,戴建业如今每天仍会留出整个上午的时间读书,基本不看手机。最近为了准备B站的唐诗欣赏付费课程,他开始重读《拉奥孔》、《艺术哲学》、《文心雕龙》、黑格尔的《美学》及唐代诗歌,“一本本原原本本地读、写笔记”,正如他对自己研究生的要求一样:读书笔记要从作者写了什么、如何写,到最后写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听来的学问是要不得的,要系统地读书。”戴建业说。
他还记得自己跟着曹慕樊老师读研究生时,曹老师不是讲高屋建瓴的概论,而是一首首地带他们细读李白、杜甫和韩愈的诗,文献学领读向歆父子、汉志、隋志,反复和他们强调,必须面向原典而非“几经转手的概论”。
“浪漫得要死,狂得要命”,这是形容戴建业时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来自戴建业课上形容盛唐诗坛的句子。可现下,面对书桌边堆积如山的待读书籍,被形容为“浪漫”本身的戴建业抑扬顿挫地在电话那头说:
“我的生活,每天除了读书就是睡觉,睡起来又是读书、做事,咳,没有半点浪漫可言!”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