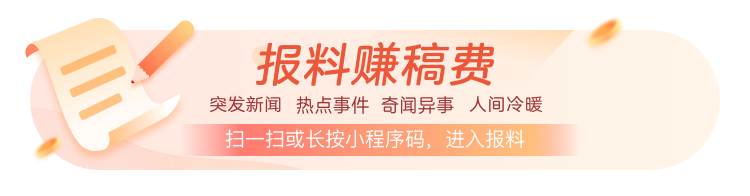“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总要觉得她会不会在诬告?”

▲ 韩国电影《素媛》改编自发生在韩国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幼女性侵案件,该片直接推动了化学阉割法在韩国的施行。“素媛案”罪犯原型将于2020年刑满出狱,80万人请愿对其实施化学阉割。图为《素媛》剧照 (资料图)
“为什么罪犯能够胁迫得逞?这一点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很多时候,正是主流社会放大了性的污名效应。本来,一个女孩被别人拍了裸照,她的人格和价值并没有减损,但主流社会观念可并不这么认为,人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她,好像她被人拍了裸照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有一个人喊抓小偷,我们就相信他遇到了偷窃,一般来说不会觉得他在冤枉别人。但是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总要觉得她会不会在诬告?会不会是翻脸后陷害?关键是很多性犯罪的证据会不会得到采信。这个跟得到授权处理这类案件的人的观念,包括性和性别观念有关。如果这些证据格外难得到法官、警察的认可,报案就很难,报案之后立案又更难。这里面是观念在影响。”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2020年4月13日,韩国“N号房”案件主犯赵主彬被送上法庭。据韩国媒体报道,他涉嫌威胁至少25名女性拍摄性剥削视频,其中包括未成年人,并分享到他运营的38个“博士房”中。
受害女性中包括知名女明星,警方调查发现,一位女演员和一位女团成员摆着“博士”要求的特有手势拍摄了照片。赵主彬利用两位女艺人的照片进行炫耀,宣传“博士房”。
要求惩罚所有观看者的舆论在韩国不断高涨。韩国警方确认了“博士房”中超过七十名收费会员的信息,对三十多人以持有儿童性剥削视频的嫌疑进行了立案。这些人大部分是20-30岁的男性,还有一些十几岁的青少年。
3月27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首尔跳江自杀,遗书写道“把钱汇进了博士房,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4月10日,一位28岁男子在仁川公寓自杀身亡,遗书自述他存有“N号房”的照片,警方在他手机内发现了三百多张儿童色情照片。
中国媒体披露了国内版“N号房”。不少儿童色情网站含有未成年男女遭受性侵的内容,一家儿童色情网站的会员多达八百万人。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宣布,将组织开展行动,对传播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有害信息现象,作出专门部署。
“高管疑性侵养女案”也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已派出联合督导组赴山东,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针对近来广受关注的性犯罪问题,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性别研究学者、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冯媛,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赵军。
1
如何界定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
南方周末:近期鲍某某涉嫌性侵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什么情况下可能构成犯罪?
赵军:我们国家规定的自愿年龄线是14岁,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性同意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未成年,《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即2013年10月23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一个提示性的规定,即“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这个规定是对刑法强奸罪“胁迫”要件的解释,而非突破。所以,不是说有特殊关系或“优势地位”存在就一定构成强奸罪,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行为人是否利用这种特殊地位或境况迫使被害人就范,也就是是否违背了被害人的意愿。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警方心无旁骛认真严格依法办案,实事求是,不枉不纵。只有依法才有正义。
至于在立法层面,有人要求提高自愿年龄线,比方说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这个年龄是16岁。对于这种呼吁,我觉得应该特别慎重。最近几年,一方面一些儿童保护人士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例如降到12岁,因为多起恶性杀人案件(被害人往往也是儿童)的加害人只有12岁,但另一些儿童保护人士又希望把性的自愿年龄线提高到16-18岁。这其实是矛盾的,难道性行为是比杀人更复杂、更难以认识、更难以决断的行为吗?这条线设置过高或过低,都会引发一系列不利于未成年人自身成长的负效应。从目前全球立法实践和我国未成年人身体发育及社会化状况看,自愿年龄线设置在14岁并不低。
冯媛:如果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加强对已满14岁未满18岁的女孩的保护,就应该删去《意见》中实际上为行为人免责的措辞,改为——对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下一步,应该推动刑法关于强奸罪名和定义的修订,现有规定已经不符合目前对性侵犯罪的国际共识;应该从侵犯性自主权的角度拟定罪名,并超越传统的狭义的“性交”说,特别是数位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性侵形式。还有,受害者应该包括男性,现实中不少男性,特别是男童,受到主要是男性实施的强暴。
南方周末:包括“N号房”在内,很多性侵的受害者是未成年人。针对未成年人的性暴力,施害者可能存在什么特殊心理?
冯媛:性心理、性的兴趣也是以男性为中心来建构的。例如恋童,尤其是对幼女、少女的兴趣,在这种结构里对纯洁、幼稚、天真、无邪等等的崇拜,也会导致某些人对幼儿、少年的欲望。对方越是少不更事、白璧无瑕,可能就越让某些人更有征服的欲望,另外,也因为她们更容易被掌控、被剥削。
2
受害者能克服恐惧并自救吗?
南方周末:“N号房”的主犯用公开个人身份和裸照来要挟受害者,导致对方不敢求助。面对胁迫,受害者有求助的机会吗?
冯媛:很多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都是受害者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逃出来,或把信息传递出来,很多案件得以侦破就是受害者求助的结果。受害者其实有很多求助行为,只是这些求助没有被看到、被识别、被重视,特别是被媒体报道出来。
首先我们一定要看到,受害者绝对不是束手无策的,只等待什么超人、救世主或偶然因素才把她们救出来,她们一定有很多抵御、反抗和求助的行为。其次,这些暴力如何让她们无法求助或不敢坚决地求助?很重要的一点,它的机制就是要建构你的心态,制造恐惧,你担心任何一个不顺从的行为都会遭至进一步的伤害。不管这个伤害来自于施暴者,还是来自于事情被曝光之后引起的社会反响,或身边重要的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这种恐惧造成了她不敢去求助,也让有的受害人甚至可能最后变成了施暴者的同伙——她觉得我已经这样了,只有跟施暴者绑在一起,我可能不那么孤单,你还是我的一个支持性力量。在家暴中有时也有体现,你会看到报警以后,警察去了,当事人说我们没事、刚才是误会,其实她这个时候是出于恐惧或讨好施害者来防备之后的伤害。如果不看到这一点,而放弃救援或责备受害者,就进了圈套。
南方周末:受害者如何能够克服这种暴力机制下的心理恐惧?
冯媛:受害者的习得性无助,很大程度来自没有外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旁观者,要做到不诿过于受害者,消除责备受害者的文化(心理),这是打消受害者恐惧的第一步。因为她的恐惧不是凭空想象的,有社会的现实依据,她知道一旦事情暴露,可能施害者受到的惩罚还不如她自己受到的惩罚更加严重。
这也需要我们的服务提供者和执法者,警察、检察官、法官,对这些行为有意识,不要评判当事人,觉得不检点或怎样。当受害者去报案的时候,不要对性行为的细节饶有兴趣,而忽略当事人痛苦、拒绝、愤怒的表达。
这样,当事人才有克服恐惧的底气。当某个人要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你那样做的话是犯罪,之后你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南方周末:假如我们受到这种威胁,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我没有错,是否就可以克服恐惧、不惧怕裸照曝光?
冯媛: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够只要求受害者,因为受害人有方方面面的弱势。我们其他人可不可以不去看不应该看的东西?比如不去了解“N号房”里的更多细节。就像当年“艳照门”事件出来后,阿娇说自己好傻好天真,之后有人看了那些片子,就说你看她哪傻、哪天真,去骂她。其实,那些片子本不是其他人有权看的。一面对那些东西、那些细节兴致勃勃,一面发表议论,这些议论有意无意地都会造成责备受害者。
赵军:从被害者的角度来说,为什么罪犯能够胁迫得逞?这一点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很多时候,正是主流社会放大了性的污名效应。本来一个女孩被别人拍了裸照,她的人格和价值并没有减损,但主流社会观念并不这么认为,人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她,好像她被人拍了裸照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其实,我们应该建构起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她被人拍了裸照,或者和人裸聊了,我们告诉她这没什么大不了,性不是可耻的,是美好的,是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只要你愿意,拍裸照不是问题,但如果有人拿这个来要挟你,那他就是在犯罪。你应该勇敢地报警,他坐牢,你还是你。
在保护女性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和传统社会陈腐的贞洁观决裂。有时,一些推动女性保护的人士出于善良动机,为了让犯罪分子得到更重的惩罚,在舆论上采取了过度放大性侵害伤害后果的策略。一个女人遭到性侵害,那她的贞洁就没了,以后就不好做人了,身心一定遭到了不可修复的永久伤害,终身都会受到这次性侵害的影响,如此等等。这其实是在放大并建构性侵害的“被害感”,这种被建构起来的被害感可能比她实际遭受的被害更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很多女性在被人拍下裸照后,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没人知道我被害我也就没有被害),最终被迫就范,让罪犯得逞。从这个角度说,过度放大性侵害伤害后果的话语建构,也成为了这些女性被害的帮凶。
3
什么在阻碍性犯罪的惩治?
南方周末:性犯罪的取证会比其它案件更困难吗?
赵军:不能笼统地这样讲。有些性犯罪案件取证的确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性犯罪案件也有一些证明上特有的优势,比如DNA。随着手机、摄像头的普及,取证手段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熟人之间发生的性犯罪,加害、被害双方往往有一个互动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形成一系列的电子证据。这类犯罪的证明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得那么难。
冯媛:要说难,哪一个犯罪取证很容易?杀人放火、偷窃,取证不困难吗?有多少小偷是他伸出手抓住别人钱包的那一刻被抓住的?有一个人喊抓小偷,我们就相信他遇到了偷窃,一般来说不会觉得他在冤枉别人。但是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总要觉得她会不会在诬告?会不会是翻脸后陷害?
没有哪一类案件绝对取证容易,关键是很多性犯罪的证据会不会得到采信。这个跟得到授权处理这类案件的人的观念,包括性和性别观念有关。如果这些证据格外难得到法官、警察的认可,报案就很难,报案之后立案又更难。这里面是观念在影响。
如果整个社会的文化还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反而会强化男性认为自己在性方面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和主导性。所以,重要的是培植平等和尊重的文化,包括性文化。
南方周末:当下偷拍的泛滥让很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不安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冯媛:其实女性一直处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或者大家把有些不安全认为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接受了、习以为常了。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有一些危害女性安全新的方式出现了。
赵军:偷拍增多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现象,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漏洞,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都有相应的规定,这主要不是立法问题,而是执法如何跟上新形势的问题。现在的执法力度,无论是对于在宾馆里安装摄像头偷拍,还是在网络中出现的那些偷拍视频照片,都很不够。这里面反映的其实是警力有限、必须“好钢用在刀刃上”的问题。我觉得公安机关应该把执法精力更多放在有被害者的案件上来,比如相对于单纯的淫秽物品传播,涉及偷拍的违法犯罪就应该是查处的重点。
南方周末:传统观念或伦理会不会影响对女性的保护?
赵军:很多年前,我调查过一起性工作者被强奸的案件,她在被绑架后又遭到了强奸。这里面绑架是一个罪,敲诈勒索是一个罪,强奸又是一个罪,要分别评价后数罪并罚。最后,强奸罪判得相对比较轻。法官的一种观念是,她是性工作者,这种拿不上台面、不会写进判决书的观念的确会对女性保护力度产生负面影响。
南方周末:对性罪犯实施严格的惩戒措施,例如韩国的化学阉割和电子脚镣,对降低性犯罪会起到多大作用?
赵军: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只观察这部分人,释放以后注射相关药物,再犯的可能性确实会降低。但整体上,国际社会对化学阉割还是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性犯罪很复杂,不仅仅出于生物因素。有一些极端的案例,在罪犯不能以通常性方式实施性犯罪时,他也可能用其它方式(工具)实施犯罪。性激素分泌水平和性犯罪并不是简单线性关系,在白银案里就有这种情况,凶手前后持续作案十多年,后期就不是用以通常性方式实施犯罪的,而是用其他方式。
冯媛:惩罚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呼吁要让行为人受到惩罚,但是具体怎么惩罚,是不是惩罚越重,就越能有效震慑,比如化学阉割?也不是可以一举解决问题的。有些所谓性能力不行的人也实施性攻击。它不是一个狭义的性能力的问题,性欲不仅是生理欲望,也有其社会性,他要靠这种性的攻击、掠夺来满足自己某些社会心理的需求,把女性当成性对象、性玩物、性猎物,满足的不是性,而是他成就感、安全感、权力感。
我们呼吁健全法律,不是说单一地注重严惩,法律的规定和作用不仅是刑罚,法律也是改变社会文化、社会机制的方式。比如立法规定从幼儿园开始都进行适合学生年龄的性教育、性别平等教育,任何时候你要把对方当成平等的人,这样一代一代情况就会大为改善。
英国警方曾经做过预防性侵害的公益广告。他们以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喝茶为例,要和一个人喝茶,首先要问他喝不喝茶,然后问他红茶还是绿茶、加奶或不加、热的还是冷的等等。实际上改变文化观念,树立平等尊重的观念,不仅是性,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你要问对方,你需不需要?你想不想要?如果对方没有表示说要,你肯定不应该硬塞给他,一定要对方明确地同意才可以。
南方周末:“N号房”事件中,除了施害者,观看视频的男性实际上也共同参与了施害,这给我们什么警示?
冯媛:施害者之所以能把其他男性拉到他这一边,甚至让受害女性没法去求助,都是利用社会性别的这种结构性因素,包括在性方面对男女的双重标准,也就是假设男性有更强的欲望、女性是满足这种欲望的,把所有人都拉到了这样一个架构当中。
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参与观看的人自杀,作为一种自责或谢罪的方式,表明他认识到,即便自己没有直接施害某一个女性,他也成为了施害者阵营的一员。结构的罪恶性体现为主犯的罪恶性,就在于他用各种方法把这些“受益者”都绑到他的战车上了。
4
“厌女”文化背后是什么?
南方周末:“N号房”事件最令人吃惊的是会员人数多达26万,按照韩国现有人口来算,大约每200个人中就有一人观看过这些影片。这导向了一个讨论,是否应该谴责男性群体?
冯媛:这可能让一般人吃惊,但它掀开了巨大黑幕的一角,就是很多男性实际上都有这样的行为。这是暴露出来的,没有暴露出来的应该更多。所以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男性会这样?它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把女性仅仅当成性的对象、性的客体,好的话就是当成性伙伴,不好的话简直是把女性当成性的玩物,性虐待、欺凌和剥削的对象。
不是说整个男性群体注定就是如此,就该谴责。男性不是天生就一定性欲更强、在性的方面更邪恶。生物决定论的那种观点是说男性天生如此,他摆脱不了这个宿命,这是一种谴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男性无可救药了”的说法等于是承认这种现象的天然合理性,也相当于认可了它。而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说,它是构建的,是我们传统的性别观念、性别规范中认可的男性的这种东西。
南方周末:目前这些针对女性的性犯罪折射了怎样的“厌女”情结?
冯媛:所谓的性别不平等是一整套的机制。比如说,一方面要膜拜女性,把女性变成天真无邪的圣母或伟大无私的母亲来膜拜,另一方面也“厌女”,把女人当成情欲的对象并认为是祸水。它把女人分成三六九等,男人也分成三六九等,这样就可以把人分为等级,便于驾驭,但最低等级的男人,下面也还有最低等级的女人垫底。
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接触到“厌女”,只是程度不一。比如一个女人做错了事情,就会说女人就是不行。一个司机开车不好,大家可能会自然地说,瞧,那一定是个女司机。一个男人做错了事情,一般会说男人就是不行吗?顶多说这个人就是不行。
南方周末:对父权的遵从、性的压抑,是否是东亚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冯媛:儒家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家长制和父系传承。首先它保证的是父系所谓的香火相传。谁在传宗接代,生育者是女性,但是女性生出来的孩子是谁家的?为什么有处女情结,它一方面在性的等级制中构建着对女性的性欲望,另一方面也是要保证父系家庭的血统是纯正的,他的财产、血统不会被外人沾染。
但在没有儒家文化的社会,也有性别制度,有对女性的压抑、对男女双重的标准。没有必要觉得这在东亚格外不得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
南方周末:中日韩等东亚三国性犯罪的情况有什么异同?
赵军:日本的性犯罪率和韩国完全是两回事,韩国相对高很多,日本就很低,中国也是一样。尽管全世界女性都面临一些共通的问题,但把中国女性,想象成韩国、印度或者中东女性,是很不切题的。
1980年代末至今,考虑到人口和其他犯罪的增长幅度,我国性犯罪整体是稳中有降的,目前媒体对女性性侵害、性骚扰问题的聚焦有过度之嫌。我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在高校里面,女性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性侵害、性骚扰,而是诸如就业、考研(博)、男朋友、收入、健康,甚至身材等等。尤其是公平的就业机会、公平的深造机会。这并不是说不关心性权利保护问题,而是说我们要更多关注中国女性在现实中面临的那些真问题,那些问题很可能是一些“硬骨头”,而且没有流量,但对改善女性状况可能更急迫。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