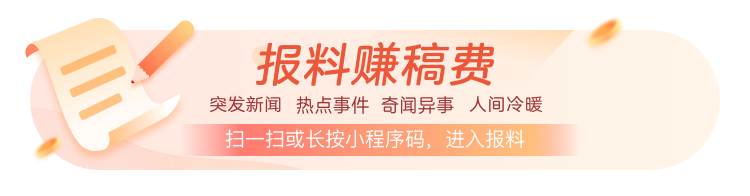揭秘|这可能是到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可燃冰科普
文章来源: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星球科学评论”,经授权转载。
文章作者:云舞空城,“星球科学评论”主编,知名地球科学类科普作者。
在遥远的中国南海,一团火焰在燃烧了两个月以后,被人们缓缓熄灭。它是蓝鲸2号海洋钻井平台的排气火炬,来自海底深处的天然气在水幕中化作火光,用这种方式重见天日。这些天然气来源于一种被一些人寄以厚望,但也被另一些人畏之如虎的物质,可燃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人们对可燃冰复杂而又纠结的心态?这需要从了解什么是可燃冰,和它“劣迹斑斑”的历史说起。


 生物遗骸腐败产生甲烷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在北国的冬天里格外常见。在封冻的湖塘冰面上,冰块里会形成一连串气泡,这是湖底有机质腐败释放的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它们随着湖水一边冻结一边聚集,在冰层里形成层层叠叠的气泡——凿冰释之可点燃。
生物遗骸腐败产生甲烷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在北国的冬天里格外常见。在封冻的湖塘冰面上,冰块里会形成一连串气泡,这是湖底有机质腐败释放的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它们随着湖水一边冻结一边聚集,在冰层里形成层层叠叠的气泡——凿冰释之可点燃。


 但巴库地区并没有形成可燃冰。自然界里,只有两种地方可以同时满足前述四种条件:数百米深的冻土带地下,或者一两千米左右的深湖/深海底部及泥沙深处。它们的温度和压力恰好使可燃冰能够稳定存在,于是也被称作水合物稳定带。
但巴库地区并没有形成可燃冰。自然界里,只有两种地方可以同时满足前述四种条件:数百米深的冻土带地下,或者一两千米左右的深湖/深海底部及泥沙深处。它们的温度和压力恰好使可燃冰能够稳定存在,于是也被称作水合物稳定带。




更多的时候,可燃冰以肉眼难以看到的状态,分散储存在泥沙颗粒之间的微小孔隙里。虽不起眼,但有着更大的储量,是目前人们勘探和试采的主要目标。

总之,这是一种主要储存在“烂泥巴和稀沙子”里的有机碳能源,它的外观和分布位置具有特定的规律。

 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则隐藏着可燃冰令人生畏的本领。
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则隐藏着可燃冰令人生畏的本领。
02


(1)围剿甲烷的三道封锁线
海底的一些微生物构建起围剿甲烷的第一道封锁线。当可燃冰分解得缓慢而稳定时,特定微生物会利用甲烷作为生命活动的原料,像植物一样为更多的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在海底构建起冷泉(cold seep)生态系统——这是一种可以养活一群奇奇怪怪深海生物的化能自养生态系统。


第三道封锁线是溶解在海水里的氧气。绝大多数甲烷气泡大多不能顺利浮上海面,而是会溶解于海水,与水中氧气发生化学反应,转变为二氧化碳和水,最终消失在海水里。

此时,地质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劣迹斑斑的古代可燃冰爆发
在距今1.83亿年前的侏罗纪早期,全球范围内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大洋缺氧事件(OAE),造成许多海洋生物灭绝。尽管尚存争议,一些科学家认为可能与大规模的海底可燃冰分解有关。

在中国试采可燃冰的南海神狐海域,人们发现距今11300-8000年前的海底泥沙有些“缺钙”——碳酸钙的含量明显偏低,这是海水酸化留下的线索之一。在排除了一些其他因素后,它被解释为末次冰期后的升温过程里,可燃冰发生快速分解引起的底层海水酸化。
除了改变海水的酸碱性和含氧量,剧烈的可燃冰分解也能改变海底地貌。
(3)地貌修改器
在挪威大陆和斯瓦尔巴德群岛之间的巴伦支海,科学家发现了令人“密恐”的景象:原本应该被泥沙覆盖得相对平坦的海底,像是爆了一脸青春痘一般,满是疤痕。

它们的深度可达10-40米,直径300-400米,更大坑洞的尺寸有600x1000m左右。在坑洞周围,海底仍在释放甲烷气泡。密集的气泡在海水里连成一串,在仪器成像里可以看起来就像是千万根火炬。

鼓包内的气体可能有两种释放途径,要么缓缓释放、海底陷落成坑;要么喷薄而出、海底炸出大坑,变成海底的“密集痘疤”。类似的地貌在全球海洋里广泛存在,中国南海同样有许多类似大坑,例如西沙群岛西南部海域800-1200米深的海底分布有密集的坑洞群,最大的坑直径有3千米左右,深度超过160米。根据它们的外观,人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麻坑。
 在陆地上,人们也在冻土地带发现过类似的现象。2014年,俄罗斯西北部Yamal半岛上,人们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大坑,周围有新近被翻出的泥土,甚是奇特。经过科学家的实地考察,发现这是因为地下气体压力过大,冲破土壤导致的一场气体爆发。
在陆地上,人们也在冻土地带发现过类似的现象。2014年,俄罗斯西北部Yamal半岛上,人们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大坑,周围有新近被翻出的泥土,甚是奇特。经过科学家的实地考察,发现这是因为地下气体压力过大,冲破土壤导致的一场气体爆发。
类似的现象在北极圈附近的冻土地带并不罕见。2017年5月,一条河道中开始产生鼓包,到了7月便炸成以一个大坑,直径达到数十米,并在爆发以后持续释放甲烷气体。
有一种解释认为,这些气爆坑的形成,与冻土地下可燃冰的分解和气体爆发有关[27]。在2014年产生的气爆坑位置,地下60米处可能存在一层可燃冰。或许正是这些可燃冰分解产生了许多无处释放的甲烷气体,它们在冻土里横冲直撞、上涌聚集,最终炸成大坑。
高压气体上浮、破坏地层的能力究竟有多强?在挪威斯瓦尔巴德群岛北部的Hinlopen滑坡边缘,一个案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人们在这里发现一处被高压天然气破坏、挖掘了将近200米厚的泥沙层。气体在泥沙地层中形成了“管道结构”,一路穿过可燃冰稳定区,至靠近海底的位置才储存起来。这样的机制可以在海底浅层制造不稳定层,具有引发滑坡的潜力。
但这只是可燃冰分解引起滑坡的一种机制,还有一种机制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海底滑坡,甚至引发海啸——那便是由于可燃冰分解引起的地层变形、强度减弱,并最终在坡度适当的地区滑落。

挪威西北部海域的Storegga滑坡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海底滑坡之一,一些科学家认为它与周期性大规模可燃冰分解有关。最近一次滑坡发生于8200年前,在挪威、冰岛、英国北部等地引发过大规模的海啸灾害,重创了当时生活在北欧沿海地区的古人类聚落。
总结下来,可燃冰分解释放出的甲烷,既可以在海底滋养生灵,也可以引起底层海水酸化和缺氧,引发海洋生物大量死亡甚至灭亡;而它们从地层里释放的方式,轻则可以引起排气鼓包或麻坑,重则破坏地层、引起海底变形或滑坡,严重的滑坡还能制造出滑坡海啸灾害。
03
未来商业开发的不确定性
尽管扮演着不安定的角色,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将可燃冰作为资源加以利用的冲动。对于可燃冰的研究大约始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的人们曾认为苏联西伯利亚的Messoyakha气田生产的天然气存在可燃冰分解释放的气体,但该结论尚存争议。真正毫无争议的、直接从含可燃冰地层里进行试验性开采,仅有短短18年的历史。
人们首先开采的是北极圈内永久冻土带以下的可燃冰,这是2002年及2007年多国合作在加拿大西北部Mallik地区的试采项目,冻土厚度650米左右,含有可燃冰的砂层位于大约1000米深。首次试采海底泥沙中的可燃冰是2013年,位于日本爱知县附近海域,这里的水深约1000米,蕴含可燃冰的砂层位于海底以下300米。


可燃冰商业化开采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如前文第二节所提,在于会改变泥沙的力学性质,降低泥沙的整体强度,容易引起海底不均匀变形、海底地层垮塌、高压气体喷出甚至滑坡等剧烈破坏现象。
例如,2013年日本试采后,一个日本研究团队的计算机模拟显示,6天的试采中,可燃冰发生分解的区域可能达到距离钻井25米的地区;如果继续生产至180天后,可燃冰分解范围可能会扩展至200米范围。而在2017年中国试采后,一支中国研究团队的另一种计算机模拟显示,可燃冰的分解会局限在钻井周围区域,即使两年后也不会超过30米。
类似这样的不确定还有很多,而仅有的几次试采结果,也并不足以打消人们的顾虑。2017年9月,中国首次南海试采结束的2个月后,科研人员来到试采海域展开环境监测。通过对比试采前、试采中和试采后的数据,认为仅在钻井过程中发生了预期内的少量甲烷释放。试采过程中和结束两个月后,未见甲烷泄露、未见海底缺氧,海底也没有发生海水浑浊度的变化,表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海底地质变化。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无论是中国的第一次试采还是日本的两次试采,均未公开海底是否发生变形的数据。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第二次海底试采中,人们使用了“未观测到甲烷泄露,未发生地质灾害”这样的字眼,这符合第一次试采后的检测结果,但同时也没有提及是否存在地层变形等方面的情况。

总之,在关于可燃冰开采引发海底变形的领域,还存在太多的空白,我们并不知道地层变形将如何累积、高压气体是否在地下聚集、何时会开始上涌破坏地层、何时会上升到海底浅层、何种条件会触发滑坡、风险会达到何种规模、滑坡是否会使附近的可燃冰失稳分解等细节。
当代海洋正处在表层海水快速酸化和缺氧的背景下,人为引发可燃冰分解和释放的前景不免令人担心。而且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海洋表层,并没有深入考虑海底可燃冰分解造成的深层海水酸化和缺氧问题。由于表层海水与深层海水的大规模交换作用(如温盐环流),最终的情况可能更糟。

海水酸化会影响部分海洋生物碳酸钙外壳的合成,缺氧海水则容易引发大面积生物死亡,二者最终会影响到海洋食物链,并以此影响到人类社会。
 虽然短期内肯定不会引起大规模生物灭绝,但势必会逐渐改变现有海洋生物的生存格局,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海洋养殖业和捕捞业,并以这种方式影响人们的餐桌——海洋为人类提供了18%的蛋白质来源,它们不光是各种生猛海鲜,还有以海洋生物作为饲料的家畜家禽。一旦海洋的生态出现问题,人类社会将会发生不小的动荡。
虽然短期内肯定不会引起大规模生物灭绝,但势必会逐渐改变现有海洋生物的生存格局,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海洋养殖业和捕捞业,并以这种方式影响人们的餐桌——海洋为人类提供了18%的蛋白质来源,它们不光是各种生猛海鲜,还有以海洋生物作为饲料的家畜家禽。一旦海洋的生态出现问题,人类社会将会发生不小的动荡。
是的,人们需要关心可燃冰开采对于海洋环境的潜在冲击,这不仅因为对于可燃冰的各种认识仍然过于粗浅,而且暂时还没有很好的监测手段和可靠模型,更因为它也能影响到你我饭桌上的食物,影响到子孙后代的食物。
也在于整个社会的你我他,能够认识到可燃冰这种物质的风险,和背后尚存的诸多未知。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