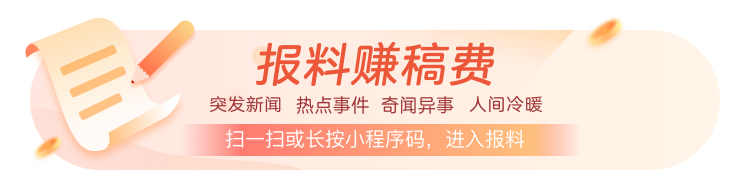赖声川:戏有戏的命

▲ 赖声川在话剧《曾经如是》排练现场。 (剧组供图/图)
“角色:一个叫时间的角色。他什么事都不做。”
这些字写在赖声川八年前的笔记上。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夏辰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八年后,“时间”真的站在上剧场的舞台上说话。时间是一个女人。还有一个角色叫“偶然”,由一位男演员扮演。
“这杯咖啡会到我们面前是有理由的,而且那个理由复杂到不行了,光是这杯咖啡已经够复杂了,它的豆子是从哪来的,它的水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你从哪来的,我们为什么约好。为什么在这一桌没有坐到那桌去,太复杂了。”赖声川说,“你可以不在乎这件事情,反正这就是偶然。”
2019年1月来到伯克利的时候,赖声川不清楚自己会导演一部怎样的戏,首先他得写出一部戏。
2019年元宵节之前,赖声川写出了16页纸的提纲。这部戏的名字是《AGO》,中文的意思是“从前”。
4月底,英文版《从前》的第一幕、第二幕在伯克利公演,时长三个半小时。
11月底,中文版《曾经如是》在上剧场公演,时长五个半小时。
赖声川最长的戏剧《如梦之梦》,在台北首次联排的时候长达12小时。后来压缩到8个小时,每天下午两点开始演出,保证观众晚上11点45前可以赶地铁回家。
“戏有戏的命,生命是有机体,每一个作品都有它这个生命该有的长度。”赖声川说,“《暗恋桃花源》用5个小时不对,《如梦之梦》不用8个小时就说不完,说不清楚。”
1
“他不会去讲不重要的东西”
上剧场的CEO是被称为“丁姐”的丁乃竺——赖声川夫人、第一版《暗恋桃花源》的“云之凡”。丁乃竺说自己不为长度担心,她为“动物”紧张。
“我不知道她紧张什么。”赖声川说。
丁姐说,这部戏的动物角色这么多,观众会不会喜欢?观众会不会以为它就是“儿童剧”。
这部戏有两百多个角色,其中几十个是动物,是国产原创戏剧中最漂亮的一群动物。戴着藏獒头饰的是一位美丽的姑娘,造型最华丽的是纽约中央公园的松鼠。最讨喜的是“恐怖的雪怪”和抓着枕头准备冬眠的熊,“没看过老鼠吵架吗”——喜欢坐纽约地铁的老鼠,因为妻子离家出走抑郁得想抽烟的纽约时代广场的鸽子,预报灾难试图拯救村民却被村民打死的狼,曾经被相信后来被“理性”不相信的雪狮……
它们分别生活在云南大山深处的乡村、纽约的街头、双子塔里、喜马拉雅山上。
“在这部戏中,或者在生活中,对动物我都喜欢,也没有特别亲近哪一种的感觉。”赖声川说。
赖声川:猫狗之间我很喜欢狗,喜欢猫的人是一种个性,喜欢狗是一种个性。猫不需要人。
丁乃竺:我妹妹就喜欢猫,她觉得猫很好,因为猫不干扰人。它存在,它也不需要你,当它需要你的时候它就过来一下,就走掉。我女儿都喜欢狗,我们两个女儿家里都有狗。我不是一个太动物倾向的人。但我发现很多人喜欢动物,我们剧场观众里有很多人喜欢动物的。
赖声川:我们以前在台北阳明山住了十年,院子很大,隔壁她父亲养很多狗。我们很忙,养不了狗。有一次可能是狗发生车祸,别人把一条狗放在我们家门口,写了一个字条,说善心人请救一下。那个狗是被撞了,我们就送到兽医那里。
丁乃竺:因为狗很小。兽医给我说,这个狗不一定救得活,因为太小了。我说你尽量救,我留了电话,救得活打给我,救不活就送走。两个星期以后他打电话,救活了。
赖声川:所以我们就多了一只狗,而且缺了一只腿,不好看。
丁乃竺:我们叫温蒂。
赖声川:结果那只狗很忠心,我们家有一堆名犬,看家都没有用,温蒂只要任何事情都在那边叫,很激动地在护着全家。大概它7岁的时候,我们要搬家了,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没有院子,狗就送掉,那些名犬很容易就送走了。最后这只怎么办?
丁乃竺:我到处去问,你们要不要温蒂。
赖声川:我还请把我们家院子打扫的人还拿了一只,他说这只不要了。后来我们真的很苦恼,商量怎么办。
丁乃竺:没有人要它。
赖声川:这是不可思议的,比我的戏还不可思议,到搬家那天它死了,自然死亡,也没有被毒死。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它在,我们在那边说,温蒂怎么办。
丁乃竺:它在,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听懂了,因为我在讲怎么办,都没有人要它。搬家那天就死在我们家窗户前面,那个时候觉得世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赖声川:所以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没什么比人生本身不可思议。如果你要对照生活中的灵感跟戏中的人物,温蒂不会对照任何一个动物,可能对照老夫妻,(一个走了,另一个也走了)。这只狗就这样来到我们家,护着我们7年,然后走了。要不然怎么解释呢?神奇地来,神奇地走。人生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戏剧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现在的人没太多耐心去看一个故事脉络展开。
丁乃竺:我还是觉得,故事是最打动人的。
赖声川:这十年来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也因此有些责任,有点像原始部落里面哪个会讲故事的(人),这个部落重要的故事他要去讲,他不会去讲不重要的东西。
丁乃竺:十年前赖老师就想做一个跟传奇有关的戏。他一直在找,也看了很多很多全世界各地、各个民族之间的传奇故事、神话故事。
赖声川:那个时候就在想做《佛经》里面的本生故事,许多是动物的,但是那些故事有点简单。
2
人类到底有多少个故事?
“从我决定用玉树故事作为口子,一下就确定了,很快,那个东西在我脑子里成型了。
在伯克利挽救赖声川故事大纲的,是他五年前为地震后的青海玉树制作的一部“疗伤剧”。“我是一股热血去做一个关于疗伤的戏,去了之后才发现已经重建的差不多了。政府动作极快,真的佩服。”
在玉树,赖声川不仅听到戴着很重头饰的不识字的歌手大段地说《格萨尔王》,也听到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地震前很多狗都叫。”赖声川说。“一个男的,家里人都死了,拿着绳子去上吊,都踩到石头上去了,听到婴儿的哭声,是个小男生,就领养了。他自己也没死。”
这个故事,发生在郝蕾扮演的雪莲身上。
雪莲是一个面馆的老板,幸福的生活在云南大山深处。灾难在一天之内同时发生了。丈夫阿福是一个想走出大山的歌手,跟着别的女人跑了。刚刚考进城里上学还没有离乡的女儿如意,死于地震。雪莲活了下来,收养的女儿也叫如意。
第二个如意死于纽约的911。这是第二幕的灾难。第三幕的灾难是一场雪崩。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于雪崩,唯有雪莲回到纽约布鲁克林,回到她的面店。
戏里的台词说:人类到底有多少个故事?三十六个?七个?六个?或者,只有一个?
“我当然同意只有一个故事。”赖声川说。
赖声川:其实我会研究不同民族的不同民间故事,有什么雷同的。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都是一样的,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条件之下,你的状态,你活着、你要死。
丁乃竺:我在伯克利上一个心理学课。那天教授就在讲,所有的故事都是死掉之后再回来。《白雪公主》是死掉了,等于睡下去了,其实通通都是人类最深的原型,其实也跟生命的轮回有关系,周而复始。
赖声川:我女儿大概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她去看电影,那个时候还在美国,就是看《白雪公主》。那年迪士尼把它拿出来重新包装了,在戏院里面放,只有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女儿还好。我觉得这个故事有好原始的东西、原型,你要说白雪公主讲季节也行,春天来了,她醒了,很深很深的。迪士尼懂这个东西。戏剧说穿了还是故事,故事怎么说有很多学问,但还是故事。
丁乃竺:国外有人说你进到剧场看故事,明明这个《暗恋》是一个通俗剧,明明这个《桃花源》就是一个大闹剧,这两个加在一起怎么是另外的东西呢?真是很奇怪。赖老师当时说我不管,我就是让它在剧场里面,你明明知道这两个剧是这样子。你真的进去看,可以被抓住。
赖声川:我有时候觉得雪莲跟布莱希特《四川好人》那个主角有关系。布莱希特没有影响我很多,虽然有个学者说《暗恋桃花源》是很布莱希特的作品。我觉得很多人不懂布莱希特,以为他就让你一直“间离”,不是,他必须让你进去才可以。你的情感要挂上这个故事才能突然被打出来。作为编剧和导演,我的责任就是这样,让你进剧场,你不要被打出来,直到我给你讲中场休息才出来。
我其实觉得《曾经如是》很简单,你如果看每个单元是很简单的,而且我的导演手法也是不复杂,就有一个莲花池是复杂的,你进到每一场戏以后,就像陈年往事一样,你进到这边,一个垃圾筒、两只老鼠,其实是很正常的,导演手法没有什么特别炫的地方。当然整体是有它炫的东西。
3
“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个人内心的宁静而造的”
“人生是不是就这样?早上和面,晚上洗锅。人生的苦到底有多久?一天、一个月、一辈子?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无法满足的苦,那为的是什么?为什么我承受了这么多,还是无法得到宁静?”
这是《曾经如是》第四幕很重要的一段台词。演员郝蕾因为这一段台词接受了这部戏。
在国外,赖声川向来被叫作剧作家。在国内,赖声川向来被叫作导演。哪里都是导演很多,编剧很少。但是在国内,只有导演更受尊重。
在伯克利公演时,《曾经如是》只有两幕——云南地震、纽约9·11。郝蕾拿到剧本时,《曾经如是》已经是完整的四幕剧本了。后两幕,是赖声川率领上剧场演剧队的演员一起创作出来的。
雪莲遭遇了所有的灾难,接下来会有什么大结局,她还能有什么念想?见到阿福。
她想在自己瞎掉以前,见到那个一夜之间疯了一样跑掉半生没有踪影的丈夫。
她在医院见到了阿福——无钱、重病、将死的阿福。雪莲把阿福带回家。疼痛的时候,阿福脱口喊出的是“美玲”——一个抛弃了他的女人的名字。
赖声川:重点还是第四幕,雪崩之后又回到纽约。第四幕很短,但是我觉得自己最多的感情放在第四幕,雪莲的那段话。早上和面,晚上洗锅,善良、正直、正义,什么事都是规规矩矩地做,所有身边的人都离开她,她得不到她真正的幸福跟快乐,为什么?我前面写那么五个多小时就是走向这个东西。
还是老先生一句话,“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个人内心的宁静而造的。”老太太说:“前面已经发生了太多事情,让后面的很多事不得不发生。”这几句话肯定是压在那儿,很重要的。”
这个戏很大的时间是在探讨人类的觉受,探讨每个人的世界是不同的这件事情。它就是说人生,想办法在短短的5个小时里面有一个对于这个世界的描述。
我常常觉得故事不是在说自己。这两天有人找我们说,有很精彩的故事,你来拍电影。不对,一般人觉得精彩的故事其实观众不一定要看。像《宝岛一村》故事不精彩,为什么你要看?这些故事在说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故事不是在说自己,这个故事在说别的事情的时候就有意思了。
我在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安排了彼得·布鲁克的戏。他九十多岁了,他越老越简单。他讲梅耶荷德的故事,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导演之死。
三个演员上台,开始说故事,讲了七十多分钟,讲完了就结束。但是观众们感动的不得了。最后故事讲完了,三个人看着观众说,真理有三种,我的真理、你的真理,还有就是真理。一分钟不说话,有个乐手弹了一首曲子结束了。这个太美了,太普通了,一点灯光效果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三个人对着观众说话。
我觉得剧场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台上一些人、台下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时代口味很重,它要的东西就是麻辣,我不知道有一天大家还能不能接受麻辣了。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