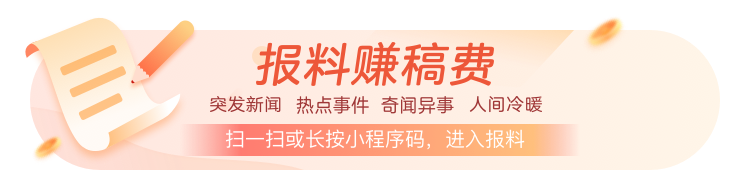南方观察|向美洲大陆上的南海人致敬

文|龙建刚
明媚的加州阳光从蓝天奔放而来,旧金山大湾区的冬天温暖如万里之外的中国岭南。从著名的金门大桥往南几公里有一片美丽海滩,滩上立有一块巨大石碑,上面刻写着四个红色大字——“中国海滩”。
这不是游人的涂鸦,而是历史性的永久纪念——
1848年后,大批华人来旧金山淘金,他们从这片可以避风的海滩登岸,并在这里扎营捕鱼晒虾。这些辛劳的华人为本地市场供应鱼虾之外,还销往美国其他地方。一片原本荒凉的海滩因华人的到来和聚集而变得热闹起来。
中国海滩曾经立有一块简陋的木牌,提醒人们记住华人为旧金山所作出的巨大贡献。1981年,一位华人历史学者向美国当局申请由他出资将“中国海滩”木牌换成花岗岩石碑。1982年6月13日,经美国国会批准,这个海滩被永久命名为“中国海滩”。它与不远处的金门大桥交相辉映,成为旧金山一个新的景点。
站在惊涛拍岸的太平洋之西,我想象这里的海水一定有来自遥远的珠江水。一百多年前,那些从东方驶来的航船里,有许许多多的背井离乡的南海人。
南海人的美洲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旧金山是我们寻访全球南海会馆北美之行的第一站。如果说马来西亚山打根是广东华侨在东南亚的望乡,那旧金山就是北美广东华侨的集散地。在遥远的旧金山,漂洋过海、闯荡世界的南海人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传奇。
美国纽约华侨博物馆这样介绍:1727年左右,3名中国海员从广州乘坐帕拉斯号航船抵达巴尔的摩,成为首批有文字记载的抵美中国人。
最早抵达美国的南海人是哪些人、是什么时候,现在已经无从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南海人比较集中前往美国的时间应该是旧金山发现金矿的1848年之后。史书记载,早期前往美国淘金的广东人主要有两波:一波是由新会、恩平、台山、鹤山、开平组成的五邑人,另一波是由南海、番禺、顺德组成的三邑人。
从广东到美国,他们走得千辛万苦。那时,坐三桅船从广州、香港出发,少则三月、多则半年才能抵达旧金山。船小人多,卫生极差;远渡重洋,苦不堪言。抵达旧金山的人们,个个形容枯槁、面无血色,有不少人病死在半路上……
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互助互保、守望相助。1850年,早期抵达美国的南海、番禺、顺德人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旅美三邑会馆。
三邑会馆早期的主要任务是迎来送往:凡是有家乡人抵达旧金山,会馆都要派人到码头迎接,先带他们回会馆住,休整两天之后,再带他们到矿区找工作;凡是有乡亲客死他乡,会馆要负责处理后事,或就地安葬,或把尸骨运回家乡。
旅美三邑会馆的会长由南海人、番禺人、顺德人轮流担任。在已经走过的170年历程中,南海人为推动三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奔向旧金山的乡亲越来越多,旅美三邑会馆所承担的事务也越来越重,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于是大家商量成立三个下属机构负责处理家乡事务:1855年,南海福荫堂率先成立,3年后,番禺昌后堂、顺德行安堂同时组建。
南海福荫堂是美国最早的南海会馆,它比全球最早的南海会馆——北京南海会馆晚31年,比最早的海外南海会馆——马来西亚槟榔屿南海会馆晚27年。这是一代人的距离,也是两代南海人的接力。
从亚洲到美洲,南海人书写了崭新的历史。

南海福荫堂坐落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心,旁边就是旧金山最繁华的金融区。这样的地段,也彰显早期旧金山南海人的眼光和辈分。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开拓者、贡献者之一,南海福荫堂今天的日子比较好过,一个很大的“福音”是旧金山南海先辈们购置的物业不断升值。
走进南海福荫堂,就是走进历史,这家“百年老店”用的是百年前的中式实木家具、悬挂的是康有为的巨幅手迹。华侨们比喻说:福荫堂就像南海人在旧金山的“居委会”,让南海乡亲的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发出华人的声音。
1920年,南海福荫堂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创办南侨学校,也就是南海华侨学校的简称,对入学就读的南海华侨子弟只象征性收取1元学费。1937年8月18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专程到访旧金山南侨学校,并在演讲中盛赞这所学校对传播中华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南侨学校至今还保留着报道陶行知这次访问新闻的《世界日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南侨学校1920年3月10日正式开学,今年正好是她的百年华诞。南海福荫堂决定于今年2月16日举行盛大庆典,隆重纪念。
穿过百年风雨,南侨学校从最初只有35名学生发展到现在的近千名学生,桃李芬芳,校友遍布全球各地,成为北美最有影响的华文学校之一。尤其让人感佩的是,一路走来,无论什么时候、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旧金山的南海人从来没有动摇办好这所学校的决心和意志。
我们到访南侨学校那天正是周末,看到满口英文的华人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努力学习中文,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动和感慨。说实话,海外的中国人很多,但像南海人那样以一己之力兴办华文学校的确实不多。他们的情怀和境界,那是很让人叹服的。


旧金山的南海人以九江最多,西樵、狮山次之。这样的人数比例也决定了旧金山南海福荫堂的权力分配:17位值理中,九江8位、西樵5位、狮山4位。从成立至今,这个规矩从来没有变过。
早期去美国的九江人之所以最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九江扼守西江要冲,水运发达,出行比南海其他地方更为便捷;其二,当年从香港、广州到旧金山的船票大约50美元一张,整个行程还要自备食粮,这笔不菲的费用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有“小广州”之称的九江经济条件较好、有钱人较多,支付能力比南海其他地方更强。
1916年,旧金山的九江人发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南海九江侨商会,一是帮新来的九江人找地方落脚,二是资助老年人返回家乡九江。1951年,九江侨领发起募捐,筹集资金买下一栋大楼,并将九江侨商会重新改组为“九江慈善公会”。1961年11月,九江慈善会发起召开第一次“旅美九江乡人恳亲大会”,全美各地均有代表参加。3天会期,盛大圆满,尽欢而散。那种历史性的场景,让美国的九江人津津乐道,也让很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羡慕不已。
九江慈善会美名远扬,无愧“慈善”二字。2016年是九江慈善公会百年庆典,时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罗林泉送了一副对联:慈悲心情系桑梓福至南海;善良人爱洒故乡德如九江。佛山市侨联如是表达祝贺:前贤艰辛奋斗举善百年赢佳名;后隽发扬光大传承千载报家国。
寥寥数语,道出非凡九江。

旧金山是美国西部南海人的聚居地,纽约则是美国东部南海人的大本营。
纽约华人扎堆的三个地方——曼哈顿下城唐人街、皇后区法拉盛、布鲁克林第八大道,到处都有南海人的身影,其中以老华侨聚集的曼哈顿下城唐人街最多。

曼哈顿唐人街的南海元素丰富而显赫:最有名的烧腊店是里水人开的,最正宗的猪杂粥是西樵人做的。离烧腊店、猪杂粥店不远处,有一座“李美步纪念邮局”,这是美国首次以华人的姓名来命名一间邮局。
邮局旁边有一座小教堂,大门上有胡适题写的文字——纪念堂。
这是一段让人动容的历史,但却是南海典籍中不曾记载的历史。在启程赴美之前,我们从未听说过李韬、李美步的名字。到了纽约,才知道这两个了不起的南海儿女,他们并且是父女关系。
李韬1861年生于南海狮山,13岁那年来到美国。先在旧金山落脚,后来到纽约学习英文并成为大名鼎鼎的牧师。他是华人社区与白人社区相互沟通的引路人,在华人中拥有巨大影响和威望。1924年,63岁的李韬在纽约去世,出殡那天,纽约华人社区停市悼念,万人送葬,极尽哀荣。
李美步是李韬的女儿,1890年4岁时随母亲从南海来到纽约与父亲团聚,天资聪颖的李美步很快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18岁那年,她以“中国的爱国主义”为题发表演讲,夺得美东地区中国留学生英文演讲大赛冠军。尽管在美国长大,但李美步没有加入美国籍,她以中国学生身份申请庚子赔款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农业系就读,192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中国经济史:关于农业》。
李美步博士毕业后,曾应陈嘉庚之邀回国到厦门大学任教,父亲去世那年她赶回美国奔丧,此后就留在美国。
李美步和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好友。李美步非常钦佩这位风度翩翩、学贯中西的大才子,胡适也把这位才华横溢、心怀理想的南海美女称为“圣女”,彼此有一段深刻的情缘。
从哥伦比亚学成回国后,胡适开始了他叱吒风云的学术和政治生涯。而从厦门回到纽约的李美步默默献身教堂、服务侨社。在那漫长的数十年里,她终身未婚,直到1966年去世。
在纽约唐人街那座小教堂里,我看到一张老照片:数十位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合影,男生西装革履,唯一一位穿着唐装的女生坐在第一排正中。她就是李美步,当年中国留学生中的风流人物。
这位南海才女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位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女性、第一位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女子、第一位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女子。
我想:人才辈出的南海历史应该补上这位南海女子的名字和故事。

枫叶之国加拿大是广东籍华侨的聚集地,当然也是北美南海人的聚集地。
加拿大早期的南海移民从19世纪50年代出现,他们有的是从旧金山北上的“淘金者”,有的是被“卖猪仔”到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建设太平洋铁路最艰险路段的劳工。
有史料记载,1863年成立的致公堂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社会组织,几个主要发起人中就有南海人。随着进入加拿大的南海人越来越多,他们又仿照旧金山模式成立了南海福荫堂,后来整体并入中华会馆。由南海、番禺、顺德三邑的黄(王)氏宗亲会已经有百年历史,成为加拿大最有影响的华裔宗亲会组织之一。
有南海人的地方总会有传奇。
美国纽约有了不起的南海父女——李韬和李美步,加拿大万锦市也有了不起的南海父子——邓汝良和邓衍锌。

今年84岁的邓汝良祖籍南海官窑,1992年从香港移民加拿大。2005年底,回到南海参加第一届全球南海人恳亲大会的邓汝良给远在加拿大的儿子邓衍锌打了一通电话,让他带上家人回家乡看看。
父子同游南海,家乡的变化让他们感慨万千,也深感加拿大的南海乡亲应该有一个组织来凝聚大家。回到万锦市,父子俩立即行动,以最快速度成立了加拿大南海同乡会。成立当天,开了26桌宴席,南海乡亲的热烈响应让他们倍感欣慰:这件事情做对了!
邓汝良出任加拿大南海同乡会首任会长,任期两年。2008年,在大多数乡亲支持下,邓衍锌接过父亲的担子,出任第二届同乡会会长,每年都会组织加拿大侨胞回家乡“寻根”。
与全球各地的南海同乡联谊会相比,加拿大南海同乡会资历最轻,但活力最强。其会员是以家庭为单位,旨在吸引老中青三代乡亲共同参与,提升组织规模与活跃度。这样的制度设计,给全球南海会馆提供了新玩法、新路子。
万锦市有一条佛山街、一条南海路。在南海对外交往的友好城市中,南海与万锦市走得最近、来往最密,背后的主要推力之一就是邓汝良、邓衍锌父子。他们把万锦带到南海、把龙狮和龙舟引入万锦,精神可嘉、功德无量。邓衍锌说:“只要是南海有任务交给我,我都尽力完成。为家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是我的志愿。”
万锦市是一个高科技企业云集的城市,被誉为“加拿大的硅谷”。万锦拥有的,正是谋求产业转型升级的南海所缺乏、所急需的。如果能在这一领域走出一条“南海路”“万锦路”,那一定是全球南海人的大事和喜事。
这个命题,当然不能仅仅依靠邓汝良、邓衍锌父子来答,而是需要全球南海人共同来做。

1906年5月,正在意大利旅行的康有为在一篇游记中写到: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
康有为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或许还不知道他的很多南海老乡早已经“游”到了中南美洲,那是地球上离广东最远的大陆。
曾经看过一条新闻:2017年3月24日,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主席梁顺到访南海,向南海有关部分介绍了秘鲁南三顺会馆以及秘鲁首都利马的唐人街的基本情况。
梁顺是南海人,中华通惠总局是1886年成立的秘鲁华侨的全国性总机构,其宗旨是总理秘鲁华侨的慈善公益事业,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维护华侨权益。
秘鲁是拉美地区华侨华人移民最多、最早的国家,秘鲁首都利马的唐人街是南美最大的唐人街。梁顺所说的南三顺会馆就坐落在利马的唐人街里。
秘鲁在19世纪独立后,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工,南海、三水、顺德一批青年因此登上了开往遥远异国的海船。据统计,从1849年到1874年的苦力贸易,有10万名中国苦力被卖到了秘鲁,被分别带往铁路、矿山、鸟粪场或种植园。
华侨华人最早来到秘鲁在种植园做苦力,华人厨师一喊“吃饭,吃饭”,华工们就到了最幸福的时候。以后秘鲁人就将中餐叫做了“CHIFA”,而且源于粤语“食饭”一词后来成为西班牙语词汇,还被收入秘鲁字典。
广东华侨博物馆有一张震撼人心的照片:一位衣衫褴褛的华人站在作物园里,他的脸上是疲惫和痛苦,而脚上戴着巨大的镣铐。这就是19世纪秘鲁华工的真实写照。
也就是这张照片,让华工的遭遇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经中国与秘鲁交涉,华工的境遇才逐渐有所改善。
劳工契约期满的华工们,在获得人身自由后要自寻工作和住所,却在陌生的社会感到惶恐无助,需要一个组织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这个背景下,秘鲁南三顺会馆于1868年应运而生,成为南海、三水、顺德乡亲们抱团取暖、同舟共济的平台。
南美洲的南海乡亲不止秘鲁一地,委内瑞拉、巴拿马、苏里南、牙买加、智利也有数量不少的南海人。
遥望那片遥远的大陆,我们心怀想念和祝福。南海永远有一种期盼和呼唤:常回家看看。

行走美洲大陆,寻访南海会馆,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转型。
其一是会馆文化的转型。
地域性社团是海外华人社会最重要的社团组织形式,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认同感和标识感。无论在美国还是加拿大,这样的地域性传统社团始终是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始终将团结互助、救贫济困、维护权益、传承文化作为基本使命。
纽约南顺同乡会副主席陈秀琼有一个忧虑:现在我们的会员普遍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已经有68岁,其实是不利于会馆传承的。

从旧金山到纽约,再到万锦,三座会馆的侨领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会馆成员年龄断层的担忧,他们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未来能有年轻人加入,将会馆文化传承下去”。
南海会馆的未来在哪里?陈秀琼的设想是“升级”:朝着“商会”的模式转型,吸引更多年轻一代加入。
其二是业态的转型。
北美南海人大部分是做生意,而且做得很出色,其中三大群体优势明显:肉食店铺行业,几乎是九江人的天下;服装裁缝是西樵人的拿手好戏、声名远扬;开古玩店则是狮山人一统江湖,雄霸一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经商的南海人越来越少,吃科学技术饭的南海人越来越多。这样的转型是南海人重视培养子女教育,愿意为此不惜代价、全力以赴的结果。北美南海华侨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几乎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少就读于世界名校。科技专业人才比比皆是,完全融入了主流社会。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向这样的南海人致敬:他们只讲求实力,从来不相信眼泪。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知名时事评论员)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