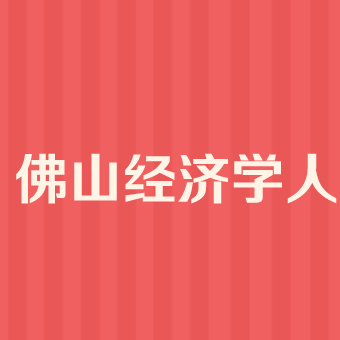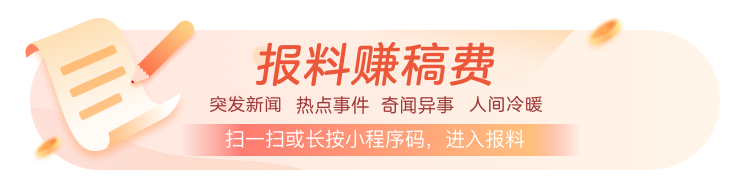品质革命 对标世界|飞利浦:小镇企业如何“点亮全球”

■编者按
荷兰的飞利浦,从小城起家,完成了灯泡生产商到世界科技巨头的蝶变;德国卡赫,把清洁机做成穿越时代与国界的大生意,把广告做到了全世界的文物古迹上;丹麦的奥迪康,从贸易跨领域切入生产,依靠创新成为助听器世界市场份额1/5的占据者……
继今年8月开展跨省调研之后,今年9月,南方日报携手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佛山市工商联和数十名佛山企业家观察员,组成调研组走进德国、荷兰和丹麦三国。
南方日报、南方城市智库正推出“品质革命 对标世界——2019年佛山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跨省跨国调研系列报道”之跨国调研篇,敬请垂注。

“Light up the world(点亮全世界)。”在坐落于荷兰的飞利浦博物馆内,写着这样一句标语。作为全球电子巨头,这句话可谓是飞利浦128年发展历程的缩影。
1891年,飞利浦诞生于一座只有6000多人的小镇——埃因霍温。这一年,飞利浦父子三人一起创业,从生产白炽灯泡起步。日后,飞利浦与通用、西门子、东芝被并称为全球四大电子集团,而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从电灯泡发迹。
但起步之初,飞利浦相比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诞生地荷兰是一个人口小国。14世纪时,荷兰人口不到100万人。即使到了今天,荷兰的人口也只有1700多万,还不到广东省的1/6。
小国里的企业,却拥有大格局。早年,飞利浦创始人兄弟中的弟弟安东·飞利浦就意识到了荷兰的市场规模太小,企业必须迅速拓展国外市场。相比哥哥杰拉德·飞利浦擅长于生产,弟弟安东·飞利浦主攻市场。在安东·飞利浦加入飞利浦的第一年,就为公司销售出20万只灯泡,此后更是带领飞利浦“照亮”全球。
在100多年前,只懂荷兰语的安东·飞利浦背起行囊,坐上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当时俄罗斯的人口总量位居全球第四。在结束21天的火车之旅后,安东·飞利浦在俄罗斯仅呆了6天,就带回了15万的灯泡订单。国外市场的助力下,飞利浦在成立后的第八年,灯泡销量首次突破100万只。
到了一战期间,安东·飞利浦的“心更大”了。他带领业务团队继续开疆拓土,直接接收了同行的欧洲“失地”,到了一战结束后,飞利浦迅速晋升为欧洲最大的照明公司。
与此同时,飞利浦也因为贡献突出,打破了荷兰私营企业需要历经百年后才能获封“皇家”称号的传统,企业在发展到第25年,就被授予皇家称号。
全球化的战略一直贯穿于飞利浦此后的发展历程。在战后,为应对各国的国际贸易壁垒,飞利浦开始走出荷兰,在欧洲各国设立分公司。到了安东·飞利浦的儿子弗里茨继任后,他延续父亲的开放眼光,把飞利浦的业务拓展到南美和亚洲,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台湾开展业务的欧洲公司。
历经一百多年,尽管飞利浦在此后的业务发展上几经曲折,但这家电子巨头一直延续着全球化的市场战略。

对于重点海外市场的深度拓展正是其中的表现。2011年,飞利浦现任全球首席执行官万豪敦在上任后,宣布要把中国定义为除荷兰和美国外的另一个“本土市场”,其对于中国这个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的重视不言而喻。
这就像是跨越百年的传承。在万豪敦的办公室内挂着飞利浦兄弟的画像。而他曾表示挂这幅画像不是巧合,“飞利浦公司在这样的注视下完成每一天的创新,我们想继续这一传统。”万豪敦说。
■对话标杆
面对兔子狐狸乌龟三类员工飞利浦如何管理?
从诞生之初起就打着“做全球生意”旗号的飞利浦,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数十个生产基地、超10万名员工。如此庞大的躯体,贯穿其中的是管理理念是什么?飞利浦负责人摩尔玛表示,人员的管理始终是最难的,那么飞利浦如何管理庞大的员工团队?
吴艳芬(广东美思内衣有限公司董事长):请教一下整个飞利浦的管理理念,以及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公司有什么不一样的?
摩尔玛:可以用动物来打个比方,第一个是兔子,第二个是狐狸,第三个是乌龟。兔子说了他就做了,狐狸说了他没做,乌龟是说不做,也没做。人群里面可以按这三种人划分,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作为一个领导要怎么办?
领导肯定是支持兔子,因为它又快又能干。但是乌龟也不见得说一定坏,因为一个公司里面只有兔子型人才也会一团糟,也需要乌龟型的人,他们冷静。领导要先搞明白这种区别,意识到乌龟的重要性,把乌龟带到兔子那边,让乌龟学习训练。对于言行不一的人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直接忽略,这些人就被孤立了。
所以,任何一个项目,总是有着这三类人,像兔子这类人他会带动整个项目的启动,然后等到兔子带动以后,乌龟这部分人其实也就出来了,然后这部分人里面一部分发生转化,一部分就消失。

梁锡强(广东福田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一个跨国企业,我想问一下飞利浦的人才是外聘的还是自主培养的?
摩尔玛:两种都有。这部分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我们会做培训,然后有日常管理,还有一个战略管理,所以我认为给他们灌输观念不是太难,不管他们是什么背景。
周建新(佛山市承安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飞利浦在推动全球创新改善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摩尔玛:人员管理始终是最难的。生产管理的核心就是需要很多方法来评估这个管理是否有效。从1980年到1990年之间,大家都在寻找这种工具。后来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人员在这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基层管理要跟火车站一样,运转精准到秒,要随时评估产品的成本、质量怎么样,交货情况如何,这些需要准时准点的方向,一个不差地达到你预想的目标。决策层的战略思想就是决定下一站你需要什么样的火车。
将基层管理要素转化成图形、数字簿和报表,叫KPI图。基层员工必须能够从这几个层面进行汇报。KPI图上显示某个东西出现什么问题,员工的报告就要跟上来。我们现在做的商业转型,就是帮助基层的人如何做这个工作。在飞利浦内部,员工会集中培训4天时间,一共有150个老师。你学会了这个流程,就可以去给下面的人培训了,你就可以拿到飞利浦内部的培训班执照。
飞利浦有过内部峰会,公司前50名高管,集聚在一起,前往比如美国大峡谷等类似的地方,具体过程比如进行徒步等。这前50名高管聚会以后会产生新想法,比如“客户第一”“精益生产”“员工是公司的主人公”等。
吴艳芬:有一种观点是,人的问题最难解决,而现在机器是越来越智能,所以不如干脆用更多先进的机器替代,你怎么看这个观点呢?
摩尔玛:这样的话或会产生更多问题。因为人工智能的复杂性,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去了解整体的人工智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或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其仁夜话
小地方为什么能做全球生意?
周其仁
1891年飞利浦在埃因霍温起家,当年这个地方就是个乡村,很穷的地方。父子三人在这里开始创业。其中三人中的父亲是银行家,银行家的特点就是对风险和机会有判断,而儿子是个对技术有偏好的人,所以父亲判断后,认为可以上技术项目。
他们以很低的价格租下了一间房子,但开始经营后情况很差、很惨。三人里面的弟弟安东·飞利浦很厉害,弟弟看哥哥和老爸这个事业不行了,就参与进来。但弟弟是个商业天才,很擅长售卖东西。
飞利浦能在小镇上成长为大公司,第一是要判断到底做什么,不能碰上一个就做,这是飞利浦父子中父亲的贡献,他做出了判断。第二是要有想象力和把想象变为现实的制造能力。什么叫制造业?制造业就是要解决问题,把产品做出来,企业家本身就有一定的想象力,对自己的动手能力有很强的信心。第三就是销售能力,你眼光判断再好,动手能力很强,没客户没市场没人埋单,最后落不了地。
所以飞利浦最后发展起来是因为飞利浦父子三人中的弟弟安东。安东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你看埃因霍温当初这么一个小地方,但是安东他的心多大,进了飞利浦博物馆,第一个介绍公司的标题是“Light up the world”(点亮世界)。他只造了一只灯泡,就要点亮世界,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仅要给埃因霍温的老百姓点灯,是要给全世界点灯。
安东一进来,定位就不是本地消费,就不是自我设限,就不是地方企业。举个例子,飞利浦发明了电动剃须刀,第一个打开的市场是哪里,据说剃须刀最早在美国卖火的。这相当于中国西北一个乡村里的人,要把东西卖到美国去。
小地方怎么冒出大公司?佛山的企业很多都是在村里、镇上办的,没有几个在中心城区办。小地方出公司,出好公司,出大公司,搞不好是个规律。现在要把这个道理挖清楚,小地方的人心反而大。荷兰1700万人,中国14亿人,我们是他的80多倍,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心反而没那么大?
荷兰也不是今天才厉害。17世纪全球3/4的海上船只是荷兰人的。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却做了全世界的生意。因为没资源,没资源就得往外闯,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温州人为什么满世界去做生意?他们人均土地连种菜都不够,无法依靠传统农业过好日子,只有出去满世界闯,所以就闯出一个“温州现象”来。这个道理是一致的。
荷兰人把船越做越好,越开越远,捕的鱼越来越多。但光捕鱼还不行,这样他们就从捕鱼跳到贸易,贸易就不光靠自然资源了,要靠人的脑瓜,要靠计算,要承担风险,所以他的贸易基因就发生在这里,荷兰人的祖先们血液里流淌的就是敢闯的基因。
心大才能界定好问题,才能界定大问题。比如我发明出来一款剃须刀,如果朝周围卖,谁愿意买谁买,没买就说不成熟,就把它摁死了也可以,无数企业就这么被灭掉了。但是如果心很大,认定这个东西人类一定需要的,这里没人买,我就去找识货的人买。

■佛山观点
竞争对手“不见了”
他们都“转”去了哪里
近十年间,德冠薄膜董事长罗维满观察到,美国、日本的同行们正逐渐在市场上消失。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被中国企业挤出了市场,但是深入了解却发现,这些同行已经转向更高端的光学薄膜领域。
当行业涌现大量竞争者、市场出现饱和时,企业利用前期积累,向高端领域转型,构建护城河,这是不少顶尖企业的成长轨迹,飞利浦也是其中之一。从2000年开始,飞利浦从消费电子领域,迈向医疗器械领域。如今,飞利浦已经是全球顶尖医疗设备生产商。
当前,佛山制造正处于从制造迈向“智造”的转型关键期,对于佛山企业家来说,飞利浦的转型路径给予他们怎样的启发?
◎创新的方向
研究往底层走,产品往高端走
【底层技术研究的成果,始终是独一无二的,不会被卡脖子的。】
陈晓峰(佛山市中格家具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智能家居方面,飞利浦做创新对底层的、基层的技术研究比较透彻。而中国的家居企业往往是在应用层做创新,应用层的创新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并且很快能够收获市场。但是飞利浦,包括荷兰这边其他的一些公司,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做底层的技术研究。
飞利浦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根据市场需求去做产品研究,实际上他做的一些产品市场并不一定需要,所以也导致市场收益不是很好,或者产品都不一定能开发出来。但是飞利浦现在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专利能够获得收益,这就是他底层研究的成果。底层技术研究的成果,始终是独一无二的,不会被卡脖子的。中国在应用层面的创新,相对来说,是容易被卡脖子的一类创新。
所以中国跟西方在创新方面最大的差距,就是一个注重底层,一个注重应用层。背后原因可能还是文化上和制度上的区别。他们的年轻人之所以敢干,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而在中国,除了有公司支持的年轻人可以这么放开干,大部分“野生群体”并没有这个基础去做,因为后面的压力很大,必须要有很好的收益,才能够继续去做这个事情。
罗维满(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飞利浦让我看到了一个大型企业转型升级成功的样本。在医疗设备领域,他是全球顶尖的企业。我也在研究全球的同行们在往哪里走,这十年间,我们的同行在日本、美国已经不见了。他们跑哪里去了呢?现在应用领域里,他们已经做不过我们了。我发现他们全部跑到光学领域去了,现在全球光学薄膜的顶级企业,都在美国和日本。看起来是我们把他们干掉了,其实他们在被我们消灭之前,已经利用此前十年或者二十年所赚的钱,全部投往高端方向。企业规模可能变小了,但是他的利润可能比以前还要多两倍到三倍。
◎创新的“套路”
要投钱,更要用科学方法管项目
【创新不但要想、要投钱,并且还需要科学的方法来管理这些钱,需要分步走,需要多方面的企业配合协作。】
李鹏程(佛山市佛晶金属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创新需要好的机遇和好的环境,飞利浦自己培育了创新的土壤,让创新的基因在这里成长。这些创新基因经过百年传承,慢慢形成了制度,或者说是科学方法。我们在国内一讲创新就是投钱、找人,但是找到人后没有科学的方法去管理。
我在飞利浦学到的东西是,创新不但要想、要投钱,并且还需要科学的方法来管理这些钱,需要分步走,需要多方面的企业配合协作。我觉得回去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在自己的企业里实践,把创新的思路或者项目分得更详细具体,把步骤都列出来,一步一步走,最终实现我们想要的目的。
张伟明(广东星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很多企业现在都越来越注重创新,但是也有不少企业还处于比较迷茫的状态,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有效率的?我们欠缺的正是“套路”,我们佛山这些企业相当需要这种“套路”。在这个“套路”里面,创新整个过程有了很明确的分工。
我自己的企业在把技术产业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碰到了这些问题,分工不清楚,造成了混乱,外行的人去干了一些内行的事情。如果能把这一块理清晰,佛山企业的创新效率会有很大的提升。
我很认可一句话:“我们应该创新,应该用中国人的魂、西方的骨架、用中国的皮肤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最高效率的创新。”这也就是中西合璧。西方企业已经在漫长的创新过程中有了深厚积累,他们肯定碰到过很多问题、吃过很多亏,然后慢慢去优化出这一套东西,我们要思考怎么把这套东西学回来。
◎创新的规则
打造新商业伦理,吸引创新主体
【埃因霍温的创新土壤让我们惊讶的地方在于,它的商业规则是谁委托谁就拥有知识产权,而且我委托你做了之后,你不能在同行业做相似的东西。】
梁锡强(广东福田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埃因霍温的创新土壤让我惊讶的地方在于,它的商业规则是谁委托谁就拥有知识产权,而且我委托你做了之后,你不能再在同行业内做相似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创新土壤促成了飞利浦以及这里其他创新公司发展到今天。
其实中国也有这种地方,几个月前,我去武汉科技大学学习,在武汉有很多比较好的大学,有一家公司手下有几十万大学生,每一个团队去创新不一样的东西。但这家公司只是一个中间媒体。
举个例子,比如罗维满董事长要研究薄膜新材料,你把提案给我,我找相关人才去做。这种公司在中国有,但是我感觉这种创新土壤我们给不了,比如说,我委托这家公司帮我创造一个东西,做出来之后马上就会有人仿作,有可能这个团队里面就有。这让我们去投入创新的时候望而却步,所以荷兰这种创新土壤让我惊讶。
李深华(广东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以阿斯麦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对原则的坚守,也就是既能够养活自己、发展自己,也能够保护投资人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实践中慢慢形成了一个圈内的共识和默契。形成了商业规则以后,可以聚集全世界所有创新主体,同时它也能够吸引有项目需求的人来这里找合作伙伴。创新主体和需求主体都能够有吸引力,就能够产生双重效应。
◇往期报道请见:

【策划】胡智勇 何又华
【统筹】林焕辉 叶洁纯
【撰文】叶洁纯 林东云
【摄影】熊程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