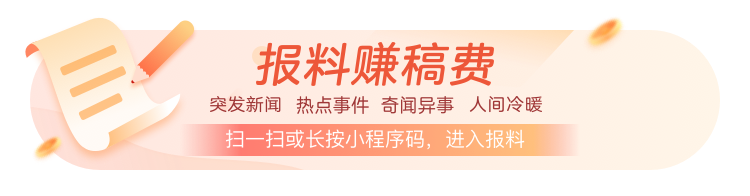对话粤籍院士| 与“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同乡,冯培德院士的“惯导”从未迷航
>>冯培德院士简介
冯培德,广东恩平人,1941年生于天津,飞行器导航制导控制专家,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系。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冯培德历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618所)所长,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等职务。他作为总设计师,主持了航空惯性导航系统国家专项的研制工作,填补了国家空白。其主持研发的惯导系统,已装备众多机种。他还在捷联式惯导、组合导航、激光陀螺、微机电系统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
110年前,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冯如,在国外成功试飞了一架自行设计、研制、生产的有人驾驶飞机“冯如一号”。这是中国人研制生产的第一架飞机,同时也揭开了中国载人动力飞行史第一页。冯如是广东恩平莲塘村人,多年以后,他的同村、同族后辈——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培德,也走上了航空报国的道路。
冯培德长期主持我国航空惯性导航系统(以下简称“惯导”)研发。他勇挑重担,率领团队自主研发出达到西方水准的惯导系统;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对前沿技术力主超前发展、跨越发展,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冯培德在离开618所后,主要精力放在了人才培养上。他认为,“自己在科技上再多干些也很有限了,但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对国家科技发展能发挥的作用则要大得多。”

大学时立志“惯导”事业
冯培德年少时即聪明好学,1948年,7岁的冯培德入读小学,面试时老师对他十分满意,同意他直接上三年级。在四年级结束后,冯培德直接跳过五年级,去了另一所学校读六年级。
读书时,冯培德始终在全年级名列前茅。甚至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他自己收集课本外的难题。1957年,16岁的冯培德高中毕业,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当时冯培德觉得,自己喜欢数学,但“纯数学没意思,最好能解决点实际问题”,就选择了北大的“一般力学”专业。
1960年,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国内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上马了一批项目,包括“09工程”项目。北大无线电系和力学系,同北航合作,进行该工程的无线电导航和惯导论证。当时在读大三,年仅19岁的冯培德,也被抽调参加该项科研,就此与“惯导”结下不解之缘。

所谓“惯导”,即惯性导航,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外界导航点、导航站、导航卫星,完全自主导航的系统,其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安全自主性;因此,在军事领域,惯导有着广泛的应用。“装了这套‘黑盒子’,就知道位置、速度、姿态、航向,这个就叫自主导航系统。”冯培德解释说。

为了便于理解,冯培德用卫星导航做对比:“卫星导航极容易被干扰,甚至卫星本身就是被攻击目标。”冯培德说,“因此卫星导航是‘用而不靠’,武器系统不能靠卫星导航。”
1967年,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冯培德被分配到陕西户县的30所(即后来的618所),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第一个从事机载设备研究的机构。此时,中国的惯导尚处于起步阶段。
从飞机残骸分析开始,经10年艰苦努力,我国第一套机载惯导——523惯导终于在1977年完成车载实验和首轮试飞,精度基本达到预期指标。
丢掉“洋拐棍”,打破技术封锁
1983年,冯培德从美国田纳西大学进修归来,担任所里的惯性导航总体研究室主任。他回国的“第一炮”就是推动采用挠性陀螺的563惯导的研究。在563惯导的研制过程中,考虑到563惯导仍然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为了在未来同国外先进战机抗衡,有必要上马更先进的航空惯导。

需求很明确,技术路径却有分歧。不少专家考虑,中国想要从文献资料上透露的只言片语自主研发,风险太大,考虑引进。
但是,与国外的谈判没能如愿进行。冯培德意识到,到了“丢掉幻想,破釜沉舟”的时候了。1989年12月14日,573惯导立项。1990年7月,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在618所的历史上,1989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年,563系列惯导563A、563B、563C三型惯导产品面临试制生产、装配调试和配合主机进行试飞试验等繁重任务;同时,573惯导也按照573通用型、573A和573B拉开了三条战线。作为惯导领军人物,已担任所长的冯培德挑起了两大系列惯导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的重任。

经10年磨砺,573惯导于1999年设计定型,达到了西方F16等主流战机的标准。但冯培德对此很清醒:“我们只是完成了发达国家20年前做的事。”
“自主研发要提前部署”
1981年,冯培德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田纳西大学进修两年。这一段经历,给冯培德带来很大的震撼。
当时,他了解到,NASA为了验证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某个结论,做了一个装有惯性传感器的零阻卫星。“这个计划做了50年,一拨一拨人接着,前面的人根本看不到什么成果。”冯培德感慨,“有一个老太太,从刚毕业就管这个项目,干了一辈子。”
冯培德告诉记者,回顾他过去主持惯导研制的过程,他认为最值得总结的不是怎么克服困难,而是要有远见,要舍得投入那些“二三十年见不到收成”的工作。“国家现在必须在这些事情上有投入,将来才能够站得住脚。”

例如,618所针对挠性陀螺的研究,要追溯到1973年。而其大规模投入使用时,已经是20多年之后了。更先进的激光陀螺,从1978年就开始了研究,到了新世纪才投入使用。1995年起,618所开始启动微机电系统研究……
“我们那个时候不上,现在得晚多少年?对于尖端技术自主研发,要提前部署。”冯培德说,“要有胆略,舍得投入,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另外,“跟跑”的日子已经过去,冯培德觉得现在更应强调“创新”。他坦承,惯导研究几十年来,虽然坚持自主研发,但基本是沿着发达国家的路径。“现在已经说不清楚它往哪跑了,基本到了并跑的阶段。下一步往哪走,就要自己开路了。”
对话:“把个人的理想、发展融入国家的需求”
南方日报:您毕业以后去了条件比较艰苦的618所,当时有怎样的考虑?
冯培德:专业完全对口,很自然就到那去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清华、北航、南航的66、67届学生有十几个人,都分配去了618所。
那时候的条件还是蛮艰苦,一开始,因为人太多了,我住过一两个月的大草棚,双层床,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开始工作。现在我跟学生们讲,要把个人的理想、发展融入国家的需求当中,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南方日报:您和“中国航空之父”冯如是同乡、同族,您也多次倡导“冯如精神”。您认为“冯如精神”在今天有哪些意义?
冯培德:冯如是第一个提出航空救国思想的中国人。他在美国时有一句话“吾军用利器,莫飞机若,势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现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很需要传承这些。我为什么不去养老,旅旅游?因为在军用领域较劲得太厉害,我们还能发挥点作用。这些杀手锏武器我们有了,才能争取不打仗,达成某种平衡。
南方日报:您近些年投入大量精力在人才培养上。您认为青年科研人员需要传承哪些老一辈的特质?
冯培德: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带队伍。现在航空航天领域总体还是不错的,三十、四十多岁的人都在挑重担。
我跟年轻人讲,你的好坏是和国家的好坏连在一起。如果国家有前途,个人也会好起来,得到应有的发展机会。要把你个人的理想跟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驻京记者】王诗堃
【策划】赵晓娜
【图片】王诗堃
转载自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