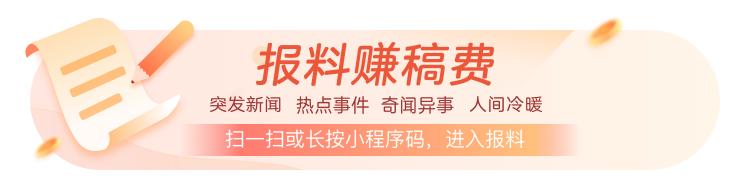大塘朗村 | 温溪派衍,塘朗源长

大塘朗村
位于大岭山之北,东与寮步相邻
总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姓氏袁,人口2000左右


据镇志记载,大塘朗村原为大松朗,明洪武元年东莞温塘部分村民迁居于此地,为记念祖籍而取名大塘朗。袁氏宗祠对联“温溪派衍,塘朗源长”也阐明其渊源。
近五年来,我不停的在大塘朗的老村巷道中行走。春末,微雨纷纷,路旁的芭蕉叶挂滴着晶莹的雨水,路湿漉漉的。走进大塘朗,那一排红粉石墙脚、立柱,青砖墙面、绿色瓦背的祠堂建筑首选映入我的眼帘,这些庄严、肃穆、古朴古香的老建筑凝聚着先贤的智慧、远古的文化和农耕时代的文明,是宗族的根之所在。这么有规模,保护得那么完好的老建筑在大岭山已不多见了。
、

袁氏宗祠(崇象堂)建于明洪武年间,坐西北向东南,占地220多平方米,前中后三进,两边有回廊,硬山顶,叠式斗拱梁架。门前石柱为八角形红砂岩石,底基莲花红砂岩石作墩,硬木质花雕斗拱梁架,船形梁脊上为雕花图案,辘筒瓦面,琉璃瓦口。门有左右各有鼓台,大门对联:“温溪派衍,塘朗源长”,其“源”取“袁”之谐音,寓言子孙枝繁叶茂,宗亲源远流长。
袁氏宗祠左右为月池袁公祠、建基袁公祠,建筑风格仿效宗祠,只是前面没有八角红砂石柱,大门两侧没有鼓台。月池公词大门对联为“月华吐彩,池墨生香”,建基公祠大门对联为“建功裕后,基业鼎新”,都寄怀着对后人的殷切期望和美好愿望。

这三大祠堂一字排列,气势央然,古民居或依其旁,或居其后,典型的古村落布局。穿行在巷陌中,古石巷道依稀可见,青砖瓦房、泥砖瓦房多也破旧零落,老房子已少有人居住,与前面的老祠堂相比,显得特别的萧条冷清。在老祠堂里闲聊的老人告诉我,现在人们大都搬迁到新围里住,但大家平时聚集在祠堂里玩,人多热闹。老祠堂千百年来作为族人聚集议事的功能并没有改变。像老祠堂这些古建筑之可以能够保存完好,得益于利用,现在都为村民的活动中心,有专门人员管理。
近年行走在大岭山的古村落中,发现许多老建筑,特别是一些具有远久历史的祠堂、堂厅都因为缺乏照料、没有修缮而败落倒塌。面对着一处处残垣断壁,不由得让人捶胸顿足,大为惋惜。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这话不无道理。


人未走近,首先传来的是袅袅的一曲岭南地水南音:“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这是《客途秋恨》,歌声不能说绕梁三日,但亲切熟悉。走进这些古祠堂,只见人声鼎沸,甚为热闹。人们都自觉结队,有一起唱大戏哼南音的,有一起聊天玩纸牌的,有围堆大杀“楚河汉界”的……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在建基公祠,待那曲《客途秋恨》演唱完毕,我轻声地问:你们会唱木鱼歌吗?
寻找逐渐遗失的大岭山木鱼歌是我到大塘朗的真正目的。老人说,都会点,但唱不好。在我的要求下,以及其他老人的捣鼓下,一个老阿婆唱起了一小段:“伤怀又见金丝蝶,雌雄一对匣中藏。你有雌雄来作伴,奴奴命薄无成双……”阿婆唱毕,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个老人告诉我,这是《金丝蝴蝶》,以前的女人都会唱。现在木鱼歌唱得最好的是“盲妹”。

木鱼歌,又称“摸鱼歌”、“盲佬歌”,自明代开始已在广东尤其东莞广为流行,有关木鱼歌在广东的盛行情况,明末清初的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写道:“摸鱼歌未阙,凉月出林间”“一唱摸鱼声,都来月下听”,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称“(木鱼歌)可劝可戒,令人感激沾襟”,民国初年邓尔雅所著的《东莞竹枝词》中有诗为证:“南音体例若弹词,书熟刚同饭熟时,从古婢宫能化俗,家家解诵摸鱼儿。”《花笺记》一书,19世纪由商人从岭南带回欧洲,1824年英国人托马斯将其译成英文,欧洲诗人歌德在72岁时读到木鱼歌《二荷花史》《花笺记》,如醉如痴,兴奋地在日记中称赞它为“伟大的诗篇”。
大岭山人历来爱唱木鱼歌,时至今天,不少老人还会哼唱一些片段。一些老年妇女还藏有一些木鱼歌本,但都是新翻印的。据说金桔村叶远堃藏有木鱼书数十本,应是个有心人了。我在本镇大塘村搜集资料时,据闻流行于民间的木鱼歌《花神托梦》,作者为该村清代举人黎大康所作。世事变迁,木鱼歌这种古巷清音在大岭山已难得一闻了。

在大塘朗村干部袁桂华的引导下,后来我和几个同事们见到了老人口中的能唱者“盲妹” 。“盲妹”竟是个男的,身材高大,本名袁石馀。袁石馀生于1948年,听他介绍,年轻时当过老师,后因角膜病没能治愈而失明。
袁石馀学唱木鱼歌是在1983年,听到了寮步镇盲人唱木鱼歌,木鱼歌声韵中特别的哀调叹唱让他感怀身世,由此坚定了学唱木鱼歌的念头。在朋友的牵线下,他拜了寮步一位知名盲人歌者为师,开启了自己的木鱼歌之路。袁石馀天赋高,很快就掌握了秦琴演奏,加上其嗓门清亮,歌声哀怨动人,很快就唱出了名堂。让袁石馀感到惋惜的是,一年后师傅不知为什么,不肯再传授袁石馀歌艺,问其原因,师傅什么也不说,也不再见他了。有同行告诉袁石馀,他师傅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识徒弟没师傅”。毕竟盲人靠技艺生活,在那艰难的日子,师傅真有这样的想法,袁石馀也表示理解,始终怀念他的启蒙之师。以后的日子,袁石馀一边在寮步、茶山一带以卖唱为生,一边不断寻求拜师学艺。直到90年代初,热衷木鱼歌的人们越来越少,木鱼歌成为袁石馀与乡亲们平日里的一种消遣。

袁石馀至今都不愿多提起那段卖唱维持生计的日子。只是即席为我们弹唱了一曲《山水鲤鱼》。他怀抱秦琴,轻弄琴弦,琴声如泣似诉。一声叹息后,袁石馀开唱了:“开书唱到鲤鱼身,有人富贵有人贫,有个罗衣穿不尽,有人无裤烂幔巾,有人筲箕剩冷饭,有人肚饿话头晕,穷在路边人不识,富在深山有远亲”……嗓色清亮、净粹,袁石馀将木鱼歌演绎得哀伤、动人,连他身边那好动的孙儿听了也静了下来。
一曲《山水鲤鱼》听罢数年,依然不时让我想起那个下午的盲人歌者袁石馀,还有那一唱三叹的木鱼歌。后来,袁石馀还尝试创作木鱼歌,并对木鱼歌定于新时代内容。他说,时代发展了,木鱼歌不应全是旧式的悲怆调子。他尝试着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事物新景象进行用心描绘,生动创作《祝大家好运气》、《东莞系个好地方》等原创木鱼歌。在2010年举办的“阳光伴我行——东莞市第二届残疾人艺术风采大赛”上,袁石馀自编自弹自唱木鱼歌《祝大家好运气》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近日我再次穿走在大塘朗的巷道中,发现那些旧民居老建筑越来越少了,五年前的许多记忆、许多镜头里的映象都不在复现了。它如同中国大地的许多古村落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我想,在送别那些印着先贤符号的古文明的同时,让我们留得住乡愁的,以后或者只能靠一些图象、一些文字了。但是,我不希望是这样!
离开大塘朗的时候,是斜阳西照时候。有一阵木鱼歌声传来,回头看去,那排红石青墙绿瓦的老祠堂在我的身后,越来越远……
完
来源 | 大岭山文广中心、大岭山报社
图/文 | 黄运生
编辑 | 穗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