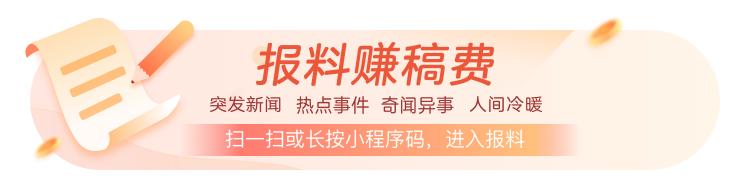织出《夏洛的网》的E•B•怀特120岁了

E•B•怀特 (1899-1985)
“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E•B•怀特以散文和评论名世,“其文风冷峻清丽,辛辣幽默,自成一格”。人们认为,他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
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和奠定当代美式英语写作规范的《文体的要素》,怀特还为孩子们写书。1938年,他从纽约移居缅因州的北布鲁克林农场,此后将“4000打鸡蛋、10头猪和9000磅牛奶”的农场生活融入三本经典隽永的童话:《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与《吹小号的天鹅》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李乃清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7956,细读大约需要18分钟
E•B•怀特79岁时曾经抱怨说:“上了年纪,实在麻烦,我始终不能摆脱我对自己的印象——一个约摸19岁的小伙子。”
这位腼腆低调的“小伙子”,曾写下令人感动一生的童话《夏洛的网》。正如书中“王牌猪”威尔伯永远铭记“蜘蛛侠”夏洛一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则关于生命、友谊、爱与忠诚的故事,依然温暖着全球无数读者,被誉为“20世纪最受爱戴的童话”。

《精灵鼠小弟》

《夏洛的网》
7月11日是E•B•怀特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十九世纪末,他生于纽约近郊佛农山,差不多年份出生的美国大作家还有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艾略特和斯坦贝克等人,此后风起云涌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些人大多踏上宏大叙事或周游世界之路,但生平“寡淡”的怀特却选择了另一种更为沉静内敛的写作——随笔和童话。
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E•B•怀特以散文和评论名世,“其文风冷峻清丽,辛辣幽默,自成一格”。人们认为,他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同世上存在“《纽约客》文风”这样一种东西。
“如果《纽约客》让人感觉其声音中有某种同一性,那也许可以在杂志的文字编辑部找到源头,那是一座坚守语法精确度和风格传统性的堡垒。《纽约客》里逗号的使用就和马戏团里的飞刀一样精确无误,一点一个准。”
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和奠定当代美式英语写作规范的《文体的要素》,怀特还为孩子们写书。1938年,他从纽约移居缅因州的北布鲁克林农场,此后将“4000打鸡蛋、10头猪和9000磅牛奶”的农场生活融入三本经典隽永的童话:《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与《吹小号的天鹅》。

“任何人若有意识地去写给小孩看的东西,那都是在浪费时间。你应该往深里写,而不是往浅里写。孩子们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他们是地球上最认真、最好奇、最热情、最有观察力、最敏感、最乖觉、也最容易相处的读者。只要你的写作态度真诚、无所畏惧、澄澈清明,他们便会接受你奉上的一切。”
终其一生,怀特都秉承“面对复杂,保持欢喜”的态度。他孜孜不倦地炮制“小”作品:小书、小人书,以及数千篇小专栏小随笔,直至早老性痴呆症蚕食掉他的大半记忆。
1985年10月1日,86岁的怀特作别了这个世界,《纽约时报》在4日发表的讣告中称:“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临终前,年迈垂危的怀特还认得周围几个亲友,儿子乔在病榻边为他念些旧文,作者是谁他并不见得全能弄清楚,但照例会问这些文字到底是谁写的。
“你写的,爸爸。”乔说。
停顿片刻,那个永远“19岁的小伙子”摆摆手道,“哦,写得不坏”。

2006年电影《夏洛的网》剧照
少年埃尔温:除了自信我什么都不缺
E•B•怀特全名埃尔温•布鲁克斯•怀特(Elwyn Brooks White),这个庄重得略显拗口的名字和他的家庭背景颇为吻合:他的父亲塞谬尔•怀特是一位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用怀特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父母,都是“体面的人”。
“我父亲正统保守,事业有成,工作勤奋,也常忧心忡忡。我母亲慈祥、勤劳、孤僻。我们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位于绿化很好的郊区,有后院、马厩和葡萄棚。除了自信我什么都不缺。”
1899年出生的E•B•怀特是全家六个孩子中最小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承受着家人最密集的关切。晚年怀特解释何以成为作家时,声称他的童年一直处于焦虑中,“我几乎事事都感到不安。”
小埃尔温常常身处悲哀或忧惧的边缘,他尤其害怕上学,年幼时,他尖叫、发脾气,哀求着留在心爱的家庭城堡,而不去幼儿园。“其实我也没受过什么苦,除了童年时人人都会经历的恐惧:害怕黑暗,害怕未来,在缅因州的一条湖上度过一个暑假之后害怕又要回到学校,害怕上讲台,害怕学校地下室里的卫生间,那里的石板小便池水流不止,害怕对于我应该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
埃尔温不是一个特别书生气的孩子,他热衷阅读,但这极少列为他的首选,尽管哥哥在他还上幼儿园时就开始教他读书了,递给他一份《纽约时报》,然后示范音节的发音规则。“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读书狂,事实上我这辈子读书很少。跟读书比起来有太多其它事情是我更想做的。我年轻时读动物故事,还有很多关于小船航行的书——这些书虽然没什么价值但就是让我着迷。”
每逢雨天学校放假,小埃尔温便兴高采烈地躲进阁楼,独自玩他的麦卡诺拼装玩具,创造属于自己的王国。然而,但凡可能,他更爱户外冒险。有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待在谷仓,男孩们上到厩楼,顺着绳索疯狂地荡下来,他喜欢那种忽而滑向地面忽而飞入半空的自由与奔放感。
1908年圣诞节后,小埃尔温在人行道上骄傲地骑起了童车,这可是小区周边第一辆童车。随着年岁增长,埃尔温越来越喜欢在户外独处,他骑自行车穿越城镇,深入近郊,时不时还要炫耀特技。(他一生喜爱自行车,1957年搬到缅因后使用的是十速自行车。)

“小时候我是圣尼古拉斯协会的成员,那里是我文学事业的辉煌起点,身上挂满了金银徽章”。少年埃尔温会用文字绘画描述他的见闻,向流行的儿童期刊投稿。9岁时,他就凭借一首关于小老鼠的诗歌,首次获得《女性居家伴侣》杂志的奖励。11岁时,他写的短文《冬日漫步》赢得了《圣尼古拉斯杂志》的银章,在他看来,这本儿童期刊做得最好的一点在于它专注动物故事。两年后,他以家中小猎犬贝波为原型写下《一只狗的真实故事》,又赢得了金章。成年后的怀特曾调侃:“11岁时,我成了一个写作傻瓜,自此逐年弱化”。
高中时代,埃尔温成为校园刊物的编辑,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偶像大多为F.P.A.(Franklin Pierce Adams)和唐•马奎斯(Don Marquis)之类的报刊专栏作家。“我敬佩任何有勇气写东西的人……我从没读过乔伊斯以及很多其他改变了文学面貌的大作家,这对我来说是件颇让人尴尬的事。《尤里西斯》我只读了大概20分钟就走人了。作者是天才并不足以让我看完一本书。但我拿到像温德尔·布莱德利写的《他们因风而活》这样的书就会被牢牢地粘在椅子上。因为他写的是一直让我迷恋(和亢奋)的东西——帆船。”
《纽约客》传奇的活见证
1917年,埃尔温考入康奈尔大学,还获得一个“安迪”的爱称。
每名姓怀特的大一男生入校都被冠以昵称“安迪”,以此纪念大学创立者安德鲁•D•怀特。埃尔温欣然接受了这个新名字,还恋恋不舍地沿用终生。
1921年大学毕业后,安迪住回佛农山父母家里,每天坐车去纽约上班。“七个月里我换了三个工作——先是合众通讯社,继而跟着一个搞公关的人干,再后来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新闻处。三个工作我没一个喜欢的。”
1922年春,安迪和大学好友开一辆敞篷T型福特车向西寻求发展,6个月后抵达西雅图,他在《西雅图时报》当了1年记者,后遭解聘,于是,他搭乘一艘草率改装的运兵船巴福德号前往阿拉斯加,后一段航程在船上靠打工完成。几乎刚一返回西雅图,他又驾着那辆车,一路做工,重返纽约。沿途零碎活计包括在咖啡馆弹钢琴、堆草垛、销售蟑螂药、卖文给当地报纸。诚如他在《非凡岁月》中所记述的:“每个人在人生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什么可以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
回到纽约后,安迪与一家广告公司签约,同时为各家报刊撰写随笔、诗歌。他搬进西十三街112号一栋四层砖砌公寓,三个室友都是康奈尔大学的同学。“房租是110美元一个月。除以四就是27.5美元,这是我能负担的数目。”
1925年2月,《纽约客》问世,9个星期后,E•B•怀特第一篇稿件《向前一步》出现在这份日后与他名字密不可分的杂志上。他靠对广告行文的戏仿之作初露锋芒,此后大半辈子为《纽约客》共撰写了1800多篇文章。
“一年夏天我出国了,回纽约后发现我的公寓里堆了很多邮件。我拿了信,也没打开就去了十四大街上的一个儿童餐厅,我在那里点了晚饭,开始拆信。其中一个信封里掉出两三张支票,是《纽约客》寄来的。总共不到100美元,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现在仍然记得那种‘这就对了’的感觉——我终于也是个专业作家了。那种感觉很好,那顿晚饭也吃得很愉快。”
1926年,《纽约客》创始人哈罗德•罗斯聘用怀特为助理编辑,怀特与罗斯、詹姆斯•瑟伯、凯瑟琳•安吉尔(后嫁与怀特)、威廉•肖恩等人一起,将《纽约客》塑造成圆熟、诙谐、高雅的文学杂志的典范。

E.B.怀特1932年4月23日的《纽约客》封面
“安迪奏响了罗斯梦寐以求的那个音符”,詹姆斯•瑟伯对怀特从来不吝溢美之词:“谁都写不出一个E•B•怀特笔下的句子来”。事实上,是怀特发掘了瑟伯的绘画天赋,杂志社办公室内,连瑟伯自己都未曾看重那些信手涂鸦,但在怀特的坚持下,两人合写的新书《非性不可?》由瑟伯亲自操刀配图。1929年,这部拿来讽刺当时黄书泛滥现象的作品蹿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瑟伯的漫画也随之获得广泛承认。经怀特力荐,《纽约客》选用了一幅瑟伯的漫画,就此开创了该杂志长盛不衰的讽刺漫画传统。
1929年对于怀特而言很重要,这年春天,他的诗集《冷美人》问世,秋天,《非性不可?》出版。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晚,在佛农山父母家中,我听到他俩谈论我那本关于性的书。父亲说,‘我不知你怎么看,但我为此感到羞愧。’这对年轻作家而言,就像当头泼了盆冷水。”10天后,怀特再次让父母感到震惊——他和一位有两个孩子、比自己大6岁的离婚女人结了婚。
新娘是怀特的同事凯瑟琳•安吉尔,她1925年应罗斯之聘担任小说编辑,直到1968年退休,为《纽约客》的小说品位赢得了巨大名声。初遇,她是这本创刊不久的杂志骨干编辑,他是刚在杂志上发表了几篇短文的作者。怀特第一次拜访《纽约客》的办公室,立刻为凯瑟琳“舒缓文学青年紧张情绪的技巧”所打动。放松后的情绪很快转化为别种情绪,此后他开始向凯瑟琳求爱。多年后,素来遣词不事铺张的怀特,追忆这场办公室恋情时,用的是“暴风骤雨”这样的字眼。
在凯瑟琳的举荐下,怀特成为《纽约客》重要撰稿人,并于1927年起担任“新闻热点”栏目编辑(直至83岁退休),由他加注的短小评语睿智而醒目,而他对时政、现代化进程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随笔也有着极具预言性的见解。“有很多年我几乎不停地思考着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混乱和残忍……我写过关于世界政府的文章……绝对主权有待淘汰。”
然而,怀特最出名的随笔作品《这就是纽约》并没有发表在《纽约客》上,1948年,《假日》杂志全文刊登了这篇长随笔。2001年,经历“9.11”后的美国人重读怀特的文字,发现53年前他们根本没有读懂这些铅灰色的预言:“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须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数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

“精灵鼠小弟”的“小划子”
约翰•厄普代克形容怀特,“他在对纽约和对缅因的爱之间徘徊”。
纽约和缅因州那个散布在他文字各个角落的北布鲁克林农场,构成了怀特生活和文字生涯的两个地理坐标。
“纽约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我爱这个城市,春天或秋天,我走到阳台上就看到隐士夜鸫在院子里啄食。也可能是白喉带鹀,棕鸫,松鸦,戴菊鸟……但不光是鸟和动物,城市风景是一道让我着迷的奇观。人就是动物,城市里充满了披挂着奇奇怪怪毛羽的人,在维护他们的领地权,在为了晚饭掘地三尺。”

1938年冬,怀特正当在《纽约客》事业顺遂之际,突然转身,携家带口从纽约移居缅因州生活。事实上,早在1931年,怀特夫妇就开始在缅因州度夏,1933年,他们在北布鲁克林购置了一处40公顷的海水农场,凭临蓝山湾。农场让两人有机会躲避市廛喧嚣:怀特驾船出海,看护动物,凯瑟琳经营花园,阅读稿件……他们成了缅因州历史上最高级的农夫。
这是个像模像样的农场,有35头羊,112只新罕布什尔红母鸡,36只普利茅斯白岩母鸡,3只鹅,1条狗(獾狗弗雷德),1只雄猫,1头猪和1只笼鼠。两位新“农夫”继续从事他们的写作和编辑。1938年至1943年间,怀特还为《哈珀》杂志撰写随笔专栏《人各有异》,近5年农村生活,怀特与动物们、独木舟和自然界朝夕相处,同时为了专栏写作,他规定自己“每天九点到十三点,要与书房寸步不离”,他声称,这段缅因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假如没有1938年移居缅因农场的决定,假如不是因为凯瑟琳长期担任《纽约客》儿童文学编辑而让家里堆满童书,假如没有那18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老缠着他讲故事,怀特或许不会写后来那三本童话。
对人群天生恐惧的怀特,始终跟孩子和动物相处融洽,他常流连于谷仓和马厩,乐此不疲地探究观察。在这些温暖的地方,他邂逅许多小生灵,最迷恋仓鼠和蜘蛛。青年远征时,他始终有只老鼠陪伴,老鼠塞在夹克或运动衣口袋里。
怀特曾说,他早在1920年代一次睡梦中就梦见了斯图尔特,这位骑摩托车的主人公是个“有老鼠特征的小人物,衣着讲究,灵活勇敢,爱刨根问底”。1938年,凯瑟琳劝他把《精灵鼠小弟》的故事写下来,但这部书直到1945年才出版,而且颇为偶然。当时怀特生了场大病,他以为自己快死了,“于是我又想到了斯图尔特”。这年春天,他把手稿交给了出版社,当看到广告上把斯图尔特说成老鼠时,怀特大为不满:“不是只老鼠,而是我的第二个儿子。”

《精灵鼠小弟》甫一出版,立即畅销,首印15个月内就卖了10万册,这个迷人的小家伙至今仍令孩子和成人神魂颠倒。但斯图尔特的故事并非电影渲染得那样惊险。怀特的原作中,斯图尔特本是为了寻找他心爱的小鸟到处流浪,走着走着却和一个袖珍姑娘攀上了交情,相约“乘上斯图尔特的小划子游河”。好不容易人家如期而至,漂亮的小划子却被人糟蹋得面目全非。人们在电影里看着斯图尔特驾机俯冲地面时紧张得手心出汗,但只有阅读故事才会在他的小划子被毁时陪他黯然落泪……
认真的孩子曾写信询问斯图尔特最终是否找到了失踪的小鸟,关于故事为何在寻找中结束,怀特承认自己也曾怀疑这是否超出了孩子的理解范畴,但他终究那样写了:“斯图尔特从沟里出来……他向前面一望无际的广阔土地看去,路显得很长。但天空是明亮的,他总感觉到,他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斯图尔特的“小划子”让人想起怀特童年收到的礼物:1910年夏天,父母送给11岁的他一条墨绿色的独木舟,小舟雅致极了,好比对他发出了通往自由和冒险的邀请。怀特浓郁的航海情结从他的随笔《非凡岁月》和《大海与海风》等篇章中可见一斑。如果说纽约和缅因是他生命中固定的两极,那么摇摆其间的是一个流动的梦:他的海,他的帆,他的永不抵岸的忧伤。多年后,这个梦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兑现:他与凯瑟琳唯一的儿子乔后来成为了船舶设计师。

动物农场:夏洛织出了“王牌猪”
“爸爸拿着那把斧子去哪里?”摆桌子吃早饭的时候,弗恩问她妈妈。
“去猪圈,”阿拉布尔太太回答说,“有一只小猪是落脚猪。它太小太弱。”“不要它?”弗恩一声尖叫,“你是说要杀掉它?只为了它比别的猪小?”接着,小姑娘说了句非常精彩的话:“我也又瘦又小,难道也应该被干掉?”
1952年,怀特织出了不朽的《夏洛的网》,讲述蜘蛛夏洛编织神奇蛛网拯救小猪威尔伯的故事,还有小姑娘弗恩,她参与了动物农场的生、死与复活。《夏洛的网》源自怀特对自家农场饲养的一头猪的命运的反思。“一天,我去喂猪,途中,忽然为它感到悲哀,因为,像别的猪一样,它注定是要死的。这让我很难过。于是我开始想法儿挽救猪的性命……慢慢地,我又把蜘蛛扯进了故事中……这是关于农场中的友谊和拯救的故事。”

《夏洛的网》来之不易,怀特写写停停两年,后又花了一年重写,出版前八易其稿。他对夏洛的所有描述来自长时间悉心观察谷仓里一只耐心又精明的蜘蛛,期间还多次向蜘蛛研究学者请教。事实上,怀特对蜘蛛的偏爱在新婚不久写给凯瑟琳的情诗《自然史》中早有呈现,蜘蛛是诗中唯一的意象。“我要像蜘蛛那样,从蛛网里将真理悟出,系一条丝线于你心上,好回到你身边去。”
无论是《精灵鼠小弟》留存悬念的结尾,还是《夏洛的网》中蜘蛛死去的伤感段落,怀特写给孩子的故事在出版社看来都不是“标准”童话,但恰恰因为深刻涉及生命的议题,他甚至打动了无数成年人。

1957年,因怀特对缅因的眷恋,凯瑟琳卸下《纽约客》小说主编一职,两人终于定居北布鲁克林农场;“定居”——用夏洛的话说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可以静静地呆着,不必满世界乱跑。当我一眼望去,就会发现什么是好东西”。前往缅因之前,怀特用《告别四十八街》一文挥别了他的纽约以及30年间住过的8个寓所,包括“有流水和良好植被,在绿宝石沙龙和联合国总部之间”的龟湾花园,而他统称它们为“栖身之地”。
《夏洛的网》以蜘蛛之死解释生命的意味,怀特最后一部童话《吹小号的天鹅》则将生命置于更为复杂绚烂的背景。“我不知灵感是何时、怎样闯入我脑海的。大概是我曾经想过,一只不能发声的吹号天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童话故事里,哑巴天鹅苦于无法表达,遇到雌天鹅时,他没法像别的天鹅那样大声倾诉“我爱你!”,于是,怀特替哑巴天鹅找了把小号,既然不能说,那就让他吹——“每一个音都像是举起来对着亮光照的宝石”。
这种窘迫怀特自己也深有体会,他从小沉默寡言。学校里要求学生当众演讲,他为此终日发愁。每每碰到这样场合,他把心里想说的写下,央求别人朗读。成名后,小到家族婚礼,大到图书颁奖礼,出席公众场合,他也是能逃则逃,连1963年政府颁发总统自由奖章他都拒绝出席,只好由一名缅因州参议员代领。四五十岁壮年时,怀特曾挑选过几家大学领受荣誉学位,虽事先灌了威士忌,那些仪式还是让他痛不欲生。“照例又是那种空虚、晕眩、华而不实的感觉将我紧紧抓住”,他给妻子写信道:“像我这样在这种事上如此无能的人,天下绝无仅有,所以谁都没法理解这样的时刻有多么恐怖。”
1960年后,凯瑟琳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跟疾病较量16年后终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怀特没有出席妻子的葬礼。举家上下无人感到意外,大家都清楚,他的这个举动,并不能抹杀他对她的毕生爱恋。
没有了凯瑟琳的怀特,一个人在缅因农场整理书稿、写书信,也继续孵蛋;他认为禽蛋是最完美的东西,因为它蕴含着生命。《吹小号的天鹅》里,路易斯从一个天鹅蛋里出来,由缅因营地起飞,一路掠过红石湖、波士顿和费城,几乎飞在整个美东的上空。厄普代克认为,这是怀特三本童话中“最无拘束,娓娓而谈”的,“它的故事给了小朋友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关于成长的寓言”。

怀特这一生,从年幼的埃尔温,过渡到成年直至老去的安迪,如他自己所言,都“走得过于拘谨”(以确保是安全的),“过于迟缓”(总在构思),这无不源于他那颗忧郁而敏感的心。安放这颗心的,有蓊郁的缅湖、有欢喜的动物,有互勉的《纽约客》,有温馨的婚姻……但正如怀特所言:“现实生活只是生活的一种——还有一种生活来自想象”。
1985年,怀特的葬礼开场,他的继子罗杰说:“即便安迪今天能来,他也不会来。”是的,老天赐给安迪一枝笔,他既然不愿说,那就让他写,他笔下每个字都闪着温柔的光,照亮无数人心底的童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