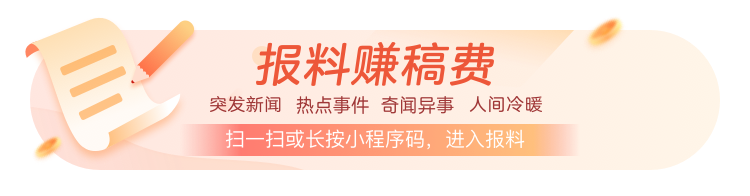游戏一场梦一场,一个成瘾少年的喃喃独白

「受访人画面及声音均已经过特殊处理」
“200多年后的世界里,将一片满目疮痍转变成欣欣向荣,我就设想自己是这片土地上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领主。”
“按照不同的角色给人员分工,粮食不够就要组织更多农民生产粮食……我可以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让活在里面的人变得更幸福。”
…………
弯腰靠在墙角的浩仔,一说起在《辐射4》游戏里的收获,一下子抬头挺胸,嘴角上扬,好像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数也变得更高。
“我好中意玩游戏,但我一点不觉得是沉迷。”
“一天才玩两三个小时而已啊”
说起被爸妈送到医院治疗,浩仔的脸又一下暗淡下来。

“是爸爸带我玩的,我一生下来,他就一直在玩游戏。现在他玩不动了,年纪大了。”
“又没影响学习,我们班男生都在玩啊!”
面对记者的提问,这个14岁的男孩不停倒苦水,问题不在自己,都是爸妈冤枉了他。
◆我係一个衰仔
“刚入院的游戏成瘾孩子,十个有八个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广州某医院青少年成瘾行为科心理医生陈泽珊一边说,一边调取浩仔的病例。从上面,记者看到“自杀”、“威胁杀妈妈”、“不想上学”、“每天吸一包烟”这几个字眼。

浩仔人前人后如此大反差令旁人很意外,“难道浩仔真被冤枉了吗?”
门诊咨询时,浩仔的父母表示,两人都很忙,以前孩子还很乖很听话的,突然这一年多来,越来越难沟通,一说什么就发脾气、砸东西,行为偏激。
入院后第3天,浩仔写下给父母的第一份信,字迹歪歪扭扭倾述着:“妈咪、老豆”:“我依家才知,离开佐你地,我係咁脆弱”………… “我唔会再乱发脾气、唔会食烟了” “平时亦唔会将自己锁在房间了,唔会作癫”…………
最后落款是衰仔。
◆45度驼背、瘦弱和战争主题
在一个上午的采访、聊天中,浩仔一直弯腰驼背,几乎弯到45度。
“这是长期坐着上网不运动造成的。”
从心理医生的讲述以及采访中,我们发现来治疗的网瘾孩子有着明显的画像特征:背弯、瘦弱、言语不多。
该院青少年成瘾行为科心理医生陈泽珊回忆起一个孩子,因为长期挤压键盘,手指指腹全部凸起;指关节粗大、变形,这是“键盘手”长期快速敲击键盘遗留的痕迹。
还有严重者脊柱出现侧弯,从身体后面望过去,他们的肩膀一高一低。长期不良姿势,或坐或侧卧、斜躺,让正处于生长发育中的孩子东倒西歪,脊椎颈椎关节已变形。

在沙盘治疗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医学科心理咨询师付爱兵医生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特别之处。
“网瘾男孩在沙盘上摆出的场景往往很典型”,如爱玩暴力游戏,就会摆出战争主题,选择的公仔包括士兵、武器、恐龙、鲨鱼、老虎等。
“对成瘾者来说,沙盘游戏是个人内在的一种体验,可让其充分表达自我情绪”,大多数网络成瘾的孩子伴有焦虑、抑郁情绪,通过玩沙盘游戏,可以在创作作品中找到自我价值和掌控感。
通过沙盘,专业治疗师能解读出成瘾少年的内心世界。
“在治疗后期,如果父母参与进来,我们可以看到亲子之间一起互动的模式和潜藏的问题等”,随着治疗继续,沙盘上的物品会慢慢朝着居家方面转变,比如车子、桥、桌椅等”。付爱兵如是说。
◆只有聊到游戏才短暂微笑
和浩仔对话时,他的眼神总在看别处;只有聊到游戏,才短暂露出笑容。
“他们完全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少家长对孩子们的描述趋于一致:拒绝你的进入,如果一旦被强行干涉,他们就会极力反对,摆出一副捍卫自己权利的姿态。

逃课、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游戏,该医院执行院长肖磊说,“我们称之为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对成年人来说,就是不能好好上班,对未成年来说,就是不能好好上课”,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有关定义,这种情况就属于“游戏障碍”。
【纵深】
探访广州首个青少年成瘾行为科:
成瘾更像是一种“果”,戒掉需要父母一起来
近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
“游戏障碍”被正式纳入疾病范畴。
官方称之为“障碍”,而非“成瘾”,可见医学界对此疾病的谨慎态度,以及社会上不可回避的争议。
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多种不同的声音。
站在产业角度,有认为把过度游戏行为列为一种疾病只会对游戏行业构成极端限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沉迷游戏的问题。有医学专家则提醒,不要单单抓着“成瘾”两个字不放,而是要看到背后的问题,尤其是家庭教育问题。
今年4月,青少年成瘾行为科在广州这家心理医院正式挂牌,并与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开展合作。浩仔成为最早一批接受治疗的患者。
院方统计,新科室运行两个月,共有过百名家属和患者的咨询和求助,但目前经过评估收治的最多只有23人(已出院的有9人),其中网瘾患者约占一半,最小网瘾患者13岁,最大25岁。而因沉迷网络前来心理咨询或治疗的青少年,其中80%以上的家庭环境都有问题。目前,根据治疗计划,现有4位患者已进入家庭治疗阶段,也就是说,父母与小孩一起入住医院接受治疗。
“家庭问题与游戏成瘾的关系,在国际上也得到业界共识”。肖磊如是说。
有一个大男孩让陈泽珊印象特别深,职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家里玩游戏。他的父亲有酒瘾,曾经在医院另一个病区戒酒瘾,家庭重担几乎都落在母亲身上,但随之而来的是,母亲对孩子的过度管控,一直到他24岁,从身份证到银行卡仍是母亲来掌管。
“男孩本想独立生活,但他母亲愣是把他住的房子放租出去了。”陈泽珊说,他原是国家队运动员,还算优秀,但最后沉迷游戏,其实也是在借助游戏表达愤怒和发起抗议。
在陈泽珊看来,游戏成瘾更像是一种“果”,“因”需要从家庭中去寻找。
◆我要与儿子和解
上周,小黄重回医院,看望曾经一起戒瘾的“战友”。
几天后电话回访,黄妈妈向陈泽珊报喜:“我的仔前天刚找到了一份工作,是自己找的!”,黄妈妈向记者感慨:“我以前劝过很多次,不要老呆在家,二十多岁了赶紧找工作,但他根本不理我,嘴巴说干都没用”。
“其实妈妈也改变很多”,陈医生悄悄告诉记者,黄妈妈以前很强势,在小黄戒瘾治疗的后期,她也一起参与进来,看到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不足,表示要与儿子做朋友,“小黄开心的一下子把手搭在妈妈肩膀上。”

陈泽珊介绍,我们戒瘾分3个阶段:脱瘾期、重建期、回归期,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孩子,最后一个阶段需要父母参与进来,一起入院治疗。“如果家庭关系存在问题,不缓解,即便在医院戒掉了游戏瘾,出院回到原来环境,孩子还是会再次上瘾,或是出现其他问题。”
一切有可能打回原形。

更多深度内容,请扫码关注。
【监制】陈韩晖 卢轶 伍青
【制片】马华
【摄影/剪辑】马华 实习生 郑浩然
【视频脚本】马华 李劼
【采写】李劼 郜小平 通讯员 谢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