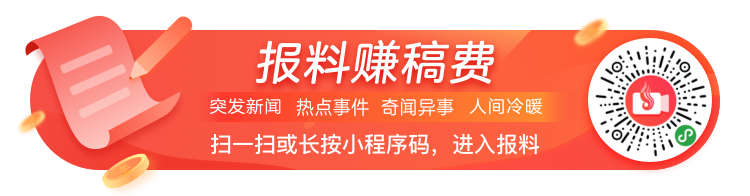【史志园地】连州城隍庙的历史变迁

古代“城”是指城邑周边的墙垣,“隍”是指墙外环绕的深沟,即没有水的护城壕。《说文解字》说“城,以胜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城隍”,为儒教《周官》记载的八神之一,也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因此,凡有城池者,就建有城隍庙。
连州城隍庙,明代以前在旧城化俗门外。明清时期,连州城隍庙在州东南城墙挨着“地标”慧光塔筑建,左侧依次为光孝寺和万寿宫,香火鼎盛,善男信女川流不息,城隍庙一带繁华热闹。
沧海桑田,到了近现代,连州城隍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最终,“一砖一瓦”都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明洪武年间,知州王彦铭迁城隍庙
我国最早的城隍庙,是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的芜湖城隍庙。至唐代,城隍信仰已颇为盛行,而且有城隍塑像。当时文人为求风调雨顺、民康物阜而书写祭城隍文。唐人张说、李德裕、李阳冰、杜牧等祭祀城隍 神的文献记载,至今仍广为流传。宋代陆游在《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中写道:“自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谨,守令谒见,其仪在他神祠上。”后对山川、城隍的祭祀亦开始列为国家祀典。《宋史》卷一〇二载:“太祖太宗时,凡京师水旱稍久,上亲祷者,则有建隆观、大相国寺、太平兴国寺、上清太一宫, 则天齐、五龙、城隍、祆神四庙 ”
宋朝的祭祀城隍还有一项内容,与出兵有关。据《文献通考》卷八十九载:“(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六月,平泽潞。及车驾还宫,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庙、社稷,仍祭祆庙、泰山庙、城隍庙。其年十月征扬州及太平,兴国四年征河东,并用此礼。”从此,诸府、州、县纷纷广建城隍庙。宋代徽宗皇帝还册封城隍,这在南宋赵与时的《宾退录》卷九中有所反映:“余尝撮城隍爵号,后阅《国朝会要》,考西北诸郡,东京号灵护庙,初封广公,后进佑圣王。大内别有城隍,初封昭贶侯,后进爵为公……盖东南城隍之盛,多起于近世,此数者亦徽朝锡命耳。”
那么,连州的城隍庙,是什么时候始建呢?
《广东通志》城隍庙旧在化俗门外,明洪武二年知府王彦铭改迁今地。据清同治版《连州志》“明知州”载:王彦铭,南昌人,监生,洪武十四年任。从中可以看出两志的记录差异,一是王彦铭任职的年份,二是职务“知州”、“知府”名称不一致。但这至少透露,连州城隍庙明代之前已建有,旧时建在化俗门外,到了明供武年间由州牧王彦铭迁来此地。
同治版《连州志》还记载:城隍庙,旧在化俗门外。化俗门在哪?由于城隍庙与化俗门、连州古城墙息息相关。査《永乐大典•湟川志腾卷)》载:连之城池,素号壮伟,宋元徽间,司徒邓阿鲁授本州剌史,实经始焉。旧城三角,岁久辄圯,城复于皇。城之门旧有五,耆老目为龟形, 曰照仁,曰化俗,曰熙平,曰熙安,曰临湟。
连州最初的三角城療初创于宋元徽(473-477年)的司徒邓鲁时期,古城门有五处,分别为熙仁、化俗、熙平、熙安、临湟,“熙仁、熙平、熙安”三门寄予着主政者对州民友爱、互助及兴隆、安定的情感,其中“熙平”更是一门双寓意,既“逢世熙平”,又忆连州历史由来,连州在隋大业中 (约610年)置熙平郡,领桂阳、阳山、连山、宣乐、游乐、熙平、武化、桂岭、开建,为县凡九。而“化俗”则“以礼理人,以德化俗”,希冀大众得以教化,风俗受德教而变化,所谓“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临湟”,即门外临州母亲河湟川。
至此,连州城之旧“化俗”门,还是难以确定其开建年代,但从州城的演化进展中,笔者推测应该在唐宋时已经有了化俗门。
另从《金史》《元史》之“礼志”中,查到城隍神尚未列人国家祀典之中,但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由于唐末藩镇割据造成封建军阀各霸一方、相互混战的局面,使得人们对城隍神的祭祀规格有所升级。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末帝李从河曾加封城隍神为“王”,在战争中以祈求城隍神的护佑。宋朝以来,各地奉祀城隍神之风更盛,各府、州、县大多数都修建了城陸庙。时代潮流,连州跟风兴建城隍庙,自然在理。当然,由于难以查实“化俗门”的具体位置,也难以查找旧城隍庙的方位,那时州城格局以“五行”布置,笔者揣测,化俗门以及城隍庙应在州城墙的东南角巽位,即今联璧路至南门大道之间。


明初,城隍神祭祀列入国家及府州县祀典
明初,城隍神的祭祀已列入国家祀典。
《明史•礼三》载:“城隍。洪武二年(1369年),礼官言:‘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不应复有城隍。故唐李阳冰《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之,惟吴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之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又芜湖城隍庙建于吴赤乌二年(239年),髙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宋以来其祠遍天下,或锡庙额,或颁封爵,至或迁就附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按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 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宜附祭于岳渎诸神之坛。’乃命加以封爵。京都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滌州皆封为王。其馀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衮章冕旒俱有差。命词臣撰制文以颁之”。“三年(1370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庙屏去他神。定庙制,高广视官署厅堂。造木为主,毁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涂壁,绘以云山。六年(1373年)制中都城隍神主成,遣官赍香币奉安。京师城隍既附繪山川坛,又于二十一年(1388年)改建 庙。寻以从祀大祀殿,罢山川坛春祭。永乐中建庙都城之西,曰大威灵祠。嘉靖九年(1530年)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旗歲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神诞,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
明太祖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后,以蒙古族为主体的 元王朝残余势力,被赶到了大漠以北。朱元璋新建的大明王朝,随时都面 临着元朝残部的反扑。洪武六年(1373年)冬十一月,元将扩廓帖木仍回兵企图强攻大同,迫使明北征主将徐达,虽有圣旨诏还,也不得不留镇 大同。蒙古骑士的勇猛骠悍,朱元璋是多次领教过的。所以立国甫定,他 就十分注重北御鞑虏,加强防卫,巩固政权。由于元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及 灾情不断,北方许多城池倾把欲摧。尤其山西各州县城更为残破。面临这 种现实,朱元璋一方面诏令修整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令 北方各府州县加固城廓;另一方面加封城隍庙,用以强化各处守军将士的 心理防线,增强自信心。按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山西通志•祠庙》 载:“城隍庙,各府、州、县,各边卫守御所俱建。本城内除阳曲、临汾、 大同三县附郭不建,凡一百有三。”更进一步验证了当初朱元捧加封城隍庙 的主要意图在于防卫。“嘉靖九年(1530年)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祭旗 霖日,并祭都城隍之神。”(《明史•礼三》)“旗纛”之神为“军牙之神”,以城隍并祭,可见至明朝中后期,防卫仍为城隍神的重要职能。
明朝政权得以稳固以后,城隍庙的功用,逐渐被转变为“鉴察、司民、显佑”,并司冥间事务。庙制和同级衙署等同,连州城隍庙亦然。明 万历五年(1577年)登进士的连州籍御史曾象乾,于明万历十三年撰写的 《重修城隍庙记》,其中记载可窥豹一斑:连州城隍庙,国初迁今地,始新于宏治,再新于嘉靖,讵今甫四十年,而庙遂颓敝,非往昔。万历甲申,州牧时丽衰公,召义耆陈九韶、陈梦麒等而谓之曰:“刺史与神,实相表里,刺史之居官有廨,吏有舍,而神之庙貌不称,刺史讵能宁其居也。自余来连,谷凡三稔,岁无天瘥,非刺史之力,神实司之。剌史力不能新神之 庙,成刺史之志,以妥神之灵,非若辈责耶?刺史其捐俸若干以为倡,若辈其终之。“民闻刺史言,踊臟事,工始甲申之春,踰年告成。”
记中所言,连州城隍庙于明代初年迁至今地重建,先后于弘治、嘉靖年间进行过修缮。明万历甲申年(1584年),以举人知连州的江南海门人时一新,找来德望公正的老者陈九韶.陈梦麒等人,商议重新修建城隍庙,安排妥当神灵,并带头捐俸禄,倡议民众一起来实现这个愿望。州民听到刺史的一番话以及看到他的善举,都踊跃地参与到修建城隍庙的工程中。
曾象乾将州刺史和城隍神相提并论,说明明代时连州城隍庙既是国家 正祀的重要场所,也是官员自上而下改良和教化基层社会的重要场所。明王朝统治者,利用民众的宗教信仰,达到其巩固皇权的目的。官员们告诫平民莫违王法、莫干坏事,否则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即使你能“蒙混过关”,也无法“瞒天过海”。城隍神主司生死善恶报应,成为维护皇权、牧司地方的守护神。

清同治四年,知州袁泳锡重修城隍庙
不仅朝时官员钟情于城隍庙的顶礼膜拜,清代地方官在其到任之初,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亲自前往城隍庙拜谒,城隍庙成为举行祈雨等 仪式及公审诸事务的场所。
清同治四年,下车伊始的知州袁泳锡踌賭满志修庙。
袁泳锡,字云舟,山东历城县进士,翰林院检讨,记名御史,广西学正揀发广东候补知府。同治四年署理连州,风格高骞,爱士恤民。连值兵燹火之余,公项耗散,乃捐廉膏火,月课书院生童于署内,训迪殷勤,士风丕振。尤心切民瘼,严禁佐杂,衙门不得擅受民词,以清吏治,民赖以安。时州志残缺,公为设局续修,去连之日,士民饯送者遮道。
袁泳锡在《重修连州城隍庙记》写道:“余于同治四年二月捧檄署理州篆,下车拈香目睹,各庙芜芜,而城隍庙为尤甚。山门颓败,垣墉倾圮,两廊向有十王神像及善恶获报故事,今皆无存。正殿神像亦颇黯然, 况旧材大半蚀朽,倾覆堪虞,为之恻然而悯悚然而惧。 ”
连州城隍庙的荒芜颓败让这位知州彻夜难眠,“窃念城隍神,固与州剌史分理幽明者也。神道设教,所以济王法之,不逮关乎政治者,甚钜而陵替。如此观感无从,则风俗人心益不可问。官斯土者可漠然乎?”
“予于是慨然有重修之志,而时值发匪汪逆,由金陵窜扰闽漳,复由闽漳扰我粤之嘉应。我官军时时获询贼情,知伊有由连阳回窜粤西之耗。统兵官飞缴来示,乃稍不先其廳,日与绅商筹划防务,不遑麵。迄次年正瓦欣闻捷音,全境荡平,予乃复理前说,而或谓予曰:约工料非三千金以外不可,君纵能倡助,不过数十分之一,雜资之百姓,连年兵燹,地方拮据,安得有此余财?是君之志甚优而力则甚绌也,且粤东旧章,凡署 任官每以周岁为限,转瞬春仲瓜期在即,始谋尚未就而替人已至。”尽管 有修城隍庙的志向,但由于匪患娼獗,加上地方财政没法实施。
面对困境,袁泳锡没有气馁。他写道:“是君之志甚宽,而时则甚促也,盖留以倭后人乎?予曰:不然!吾亦只知行吾志而已,至力之优绌,时之宽促所不计也,乃进绅士等而示以志。众皆欣然,遂捐资为倡,并示谕绅商,量力布施。”
“是年三月,居然开工。撤旧更新,规模较前增大,更加壮丽。神像亦重塑,庄严令人瞻仰起敬。至今年十月告竣。予则初经卸篆,犹及见其落成,拈香安神位焉。呜呼!统计所费不下四千金,不可谓非银款,而竟能不缺于用,且以其余力修建接官亭之牌坊,以壮郭外之观。”终于,经过筹备和大半年的动工建设,城陰庙不仅修缮完毕,还有余款修建接官亭膽。
城隍作为汉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是汉族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地方官对城隍庙情有独钟,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隍庙就是帝国统治体系的一部分, 而不只是一种象征。一方尊崇的官员,希望死后被封为城隍,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地方百姓自发地为政绩突出的官员建庙祭拜。如连州吴公祠,在城隍庙内,祀明吏目吴中选太史,陈子壮赞,知州陶德焘记,后改为四公祠。今记。吴中选,吴江人,值徭排倡乱迫近,都邑公率乡勇挺戈战,以众寡不敌,与仆吴成同遇害,州人立庙祀之。

城隍庙繁荣城隍街市
由于官员的重视,使得连州城隍庙周边逐渐繁华起来,成为了一处繁荣街市(即今城隍街一带)。“每逢城隍出巡,整座城市喧嚣鼎沸,接连不断的游神队伍,吹吹打打的戏班子以及那些赎罪的香客,成为大规模驱鬼游神的活动中心。”今古稀之年的连州街坊袁雨光回忆说。祖辈一代曾告诉他,明清时期,连州城隍庙庙会商品种类繁多、琳雍满目、应有尽有,油靴、油鞋、男女缎靴、笔墨砚台、时画圣像等。
旧时,盛典之一是城隍诞辰。原为农历三月二十八,后改为农历五月二十八,在城隍庙举行。再是城隍每年三次出巡。春季为清明日,出巡“收鬼”;秋季为“中元节”(七月十五),出巡“访鬼”;冬季为十月初一,出巡“放鬼”。每次出巡,道士先将城隍和夫人木像移至前殿,出行时,用木椅抬轿内。旧时迷信,为“祈福免祸”,为将来死后“进阴曹地府好做鬼”而打通关系,或因为替父母重病许愿,等等,于是,在“城隍出巡”之日,人们要扮成罪人,穿上红色囚衣参加送迎行列,几乎家家 如此。所以,每次“城隍出巡”,送迎行列浩大,善男信女祈福,纷紛上香焚纸,顶拜。庙内火光烛天,烟雾迷离,万头攒动。
“从1960年开始,我是在城隍庙上的小学,一直到毕业。”袁雨光说,“那时候城隍庙还算完整,不过庙里没有了神像。1966年“破四旧”城隍庙受到激烈冲击。”
袁雨光回忆说:爷爷和父亲在世时曾说,1931年红七军转战连州时,就住在城隍庙和城隍街的部分居民楼里。我家里就住过红军,他们走后,在天花板留下了一首诗……不知何日得回家。家中父母年纪老,少年妻子一枝花,传闻他们不信鬼神,一住入城隍庙就将里面的神像抬出去烧掉了。
《连州市党史资料汇编》记载:1931年1月21日(农历十二月初三) 凌晨,红军齐集在关帝庙前的操场向连州进发。当天薄暮,前锋部队从城隍街进入连州外城。……当晚,设于城隍街城隍庙的指挥部内,灯火通明,军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计划。……李明瑞等首长分别在城隍庙前空坪和学宫门前召开民众大会,宣传“本军革命之目的在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解除民众痛苦,望民众毋误听谣言”……经军民一昼夜的奋力抢救,24日黎明时分,大火终于被扑灭。连州群众感激万分,派出代表抬着百多头生猪,千余包大米,还有布匹、药材等物资,来到城隍庙红军指挥部,慰劳亲人。连州商会筹集了四万元光洋献给红军。军需得到了很好的补充,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前委首长当机立断,决定撤离连州,继续北挺。
据《抗战记忆一一连县》载:1938年11月3日,日本军机18架次首次轰炸连州,几处地点被炸,炸死平民80余人,炸毁房屋间,100多名在老人桥受伤的民众被抬到城隍庙内紧急救护。1944年,连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成立,设在连州城隍庙内,全校3个班。县政府教育科长伍啸田兼任校长。1945年1月,因有日军进入连县境,学校暂搬到龙坪元璧村上课,度过一个战时动荡的春节。
《连州市教育志(1727—1996年)》载:连师附小位于连州市区南端的慧光塔下,学校前身是解放前的升德镇、联兴镇小学。校址是用观音堂、城隍庙改建的。校旁有慧光塔和万寿宫。解放初,学校曾称为城关小学、五区一小。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夏,以城隍庙为校址,开办简易师范,招生132人。1953年一1955年,将校侧的万寿宫(水上小学)、方便医院和福建会馆等旧址划归学校,改称为城隍街小学、连州镇第四小学。1963年9月,施行新订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韶关专员公署教育局批准连县11间小学(连州镇中心小学、城隍街小学、东陂小学、 西岸小学、良江小学、龙坪小学、星子小学、大路边小学、山塘小学、九陂小学、保安小学)施行此教学计划。“文革”期间,校名先后改为安源小学和延安小学,后又恢复为连州镇第四小学。1982年4月3日县文教办发出【82】07号文,将连州镇四小改为连州师范附属小学,5月1日起执行。十多天后的5月12日,正式命名为“连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舍用观音堂、城隍街、万寿宫、福建会馆的旧屋改造而成。
2015年11月,“连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恢复为连州镇第四小学。

参考文献:
1《连州市教育志(1727—1996年)》;
2.《抗战记忆一连县》;
3.《连州市党史资料汇编》;
4.《连州志(同治版)》;
5.《永乐大典•湟川志(残卷)》;
6.刘家军沈金来主编《城隍信仰研究:安溪城腺庙》;
7.徐李颖著《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
(作者单位:连州市新闻信息中心)

本文来源于《清远古今》2018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