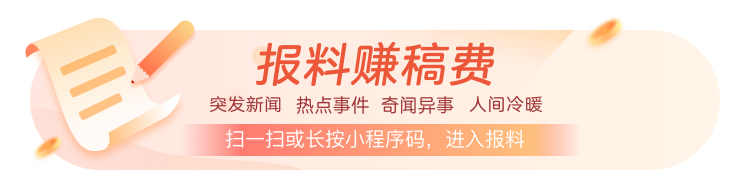荐读 | 近代百年风云激荡,广州如何华丽转型?
位于东风中路的中山纪念堂早已是广州一大地标。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设计方案出自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吕彦直之手。
在纪念堂外部,他采用了“攒尖八角亭”“重檐九脊歇山顶”“重檐歇山顶抱厦”等中式建筑元素。内部结构则被设计为拜占庭式,以钢筋混凝土和花岗岩材料替代砖木,以钢桁架拉伸的大型穹顶替代传统建筑中的梁柱。

▲中山纪念堂
位于公园前地铁站附近的人民公园,布局同样出于一位康奈尔校友——杨锡宗的构思。
公园始建于1918年(初建时称市立第一公园,后曾改名中央公园),是广州城建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园。杨锡宗在设计时并未采用传统“移步换景”的私家园林式布局,而是采用西方罗马式的对称布局,适应当时公共活动的需要,强调场所的公共性。

▲人民公园(前市立第一公园、中央公园)
离人民公园不远的广州市政府大楼(曾为广州市政府合署办公楼)则由留学法国的东莞籍建筑师林克明设计。它楼高五层,打破了传统官府平面展开庭院式布局,而黄瓦绿脊、红柱白基的外观却是中式风格。

▲广州市政府大楼(前广州市政府合署办公楼)
在长期为岭南文化著书立说的地道“老广”梁凤莲眼里,这些建筑师们颇具开放意识,他们的技术支持是当时广州在城市更新中迅速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是一批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使广州在20世纪初完成了中西文化兼容。
她将这些写进了自己去年出版的新作《百年城变》。在《百年城变》中,梁凤莲把目光对准广州历史上浓墨重彩的近代阶段,告诉读者这座城市在近代的一百多年间是何样貌,有何改变,因何改变,如何改变。
近期,以“立得住的城市 说得清的广州”为主题的读书沙龙在广州图书馆举行。本书作者、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谭晓红,广东新快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冯树盛,信息时报文体中心常务副主任白岚等做客沙龙。

梁凤莲,广州人,现任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一级作家,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出版有文化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专著《容度之间》《城市的拼图》《文化在场》《乱云飞渡》《佛山状元文化》等;长篇系列小说《羊城烟雨》《西关小姐》《东山大少》《巷娈》,散文专集《被命运催赶的夜晚》《远去的诺言》《广州散韵》《应愿之地》等;主编各种文集13种。

副标题: 十九世纪以来广州的城市演变与文化形成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1
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博士关于广州城市文化演变与形成的理论著作,全方位阐释了百年广州为实现梦想不断奋进的国际大都市演变进化史,多维度深入探讨了广州近百年来的迅猛发展态势和种种缘起,深层次地揭示了城市改革对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作者:受雇于伟大记忆,想写出真正认知
多年研究、书写岭南文化的作者,称自己的工作“如同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她说,假如对广州认识不到位,就可能被一些现象遮蔽。她坦言写书初衷是想让读者对广州的认识不只停留在皮毛,让他们对城市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从衣食住行层面,上升到价值观和精神层面。
都说广州重商、粤人爱吃,本书希望带读者领略广州在“搵钱”“搵食”之外的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她与读者探讨广州人低调性格的由来,认为这种低调未必就是不自信——历朝历代很多人通过大迁徙来到这里,我们的先祖可能来自中原,低调务实是因为人的来源、生态和处境所导致的品格。
一些人会因广州的平民色彩认为这座城市较为普通,而在梁凤莲看来,平民意识颇为可贵,它也是了解广州的关键切入点。

▲梁凤莲
她特别强调,广州是“立得住的城市”,也是“说得清的广州”。前者着重指广州城市文化的品格,广州的文化气质和文化价值在近现代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产生不可低估的全国性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关键城市就由广州来充当。改革开放后广州向外输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近代百年为之奠定历史和文化基础。
“说得清的广州”,则是认为广州具有非常清晰的历史脉络。建城2000余年来,特色分明的文化在此融汇蜕变,它的文化有自身的魅力,也有非常柔韧和强悍的传承力,许多民俗节庆遗存到今天。
为了说清广州,梁凤莲主张深入了解城市精神,不是停留在材料上、数字上或浮光掠影的,而是真正拿出判断、认定和重新的认知。
评价:优美文字写转型,突出广州人情味

▲谭晓红
这本书在风云变化的大历史中通过小的细节、具体历史事件帮助我们去理解,去挖掘文化的脉络,以及这些事件背后带来的意义和启示。
有几个关键词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广州,一个是图层,广州经过多次文化图层改造,以及包括了辛亥革命、鸦片战争大的历史事件的改造,形成一些文化迭代图层的累积。
第二个关键词是底色。凤莲老师提出“多元文化的价值核心”的概念,即广州形成了一种“能接纳不同文化,并且把它融合调配成最美丽的颜色”的价值观念。
第三个关键词是进化,就是出于自身的进步不断进化,在城市的发展里自己选择自己的文化是什么样的身份,自己选择要走什么样的文化道路。我们在明清两代打下了很雄厚的文化根基,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是自主选择进化而不是被播化(注:播化论学派是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人类学、民族学学派,核心观点是人类的文化很多都不是本地区人们所创造的,它们都是从其他文化起源地借鉴过来的)。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谭晓红

▲冯树盛
读书的第一点感受是,梁博士用优美的文笔进行历史写作,行文非常流畅,生动之处犹如我们做新闻的现场报道。
例如书中写到1935年胡适在香港演讲时公开批评广东很多人主张用古文、提倡读经,主政广东的陈济棠强令取消胡适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并驳斥胡适“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回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读到这段,仿佛看到胡适与陈济棠隔空叫阵。原来历史可以写得如此有趣,这何尝不是一种“场景”,与其说是在记述历史,不如说是一场“现场报道”。
读书的第二个感受是广州是可以说得清的,而且应该说是自信满满的。从书中提到的科举考试、市政建设等史实看,广州不乏人才,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广州的风貌和北方已经有很多的区别,很有“现代范”了。
第三个感受是梁老师在叙述时保持了客观的立场,跟我们在做新闻报道一样客观、中立,还原历史本身,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广州评价的差异和变化。
——《新快报》常务副总编辑冯树盛

▲白岚
书中有很多学术概念和学术的支撑,但是文字本身非常通俗,大家读出来觉得很过瘾,却需要读几遍之后才能够真正理解它所表述的内容。
我仔细读了这本书以后,发现凤莲博士比较认同文化地理学的一些研究的角度,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区域的文化特征。她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和广州近代文化的演变,也提出了近代广州城市文化的很多细节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它不是单一的因素。这个不同城市文化要素之间是一个互动、互为的结果,导致广州的文化精神到现在是这样的一种呈现。
——《信息时报》文体中心常务副主任白岚

▲沙龙现场
为了更好地观察城市史,梁凤莲选择了广州文化形成最关键的近代发展转型期(即1840年至1949年这百余年)作为考察对象。在具体研究里,她通过个人经验重新挖掘与整理史料,对广州的近代城市史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考察。
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主体演变、共治结构、商业经济、城市规划以及文化品牌,尝试“理清城市文化要素之间互动呼应的因果关系”。同时,这六个部分连缀成一条完整的线索,贯穿着梁凤莲对城市历史肌理与文化根脉的价值判断与认知。归根结底,广州之所以能成为广州,是因为它从近代这一转折期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不断创造,在蜕变中形塑出自身独特的广府文化价值。
……
书中可随处读到如“世俗”“民间”“市民”和“市井”等充满民间气息的词汇。它们均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民”,比如:第一章里谈到《南京条约》签订后民风的强硬与广州官民的反入城运动;第二章探讨近代市民文化认同意识的出现;第三章聚焦民间共治与政府管制的城市二元治理结构;第四章提到民间“求富”思想的出现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起了颠覆性的推动作用;第五章从建市规划中看出“以人为本,以市民为本,以市民的喜好为本,成为广州建市之基础、立市之根本”;第六章从近代广州著名的文化品牌研究地方文化与市民意识之间的关系等。可见,广州城市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构成其底色的正是浓烈的市民文化。
——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博士后徐诗颖
书摘
为了现实的社会需要乃至政治需要,艺术家群体的思想在近代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一些旗手人物,他们开放性地把西方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借来为我所用,创造了独特的“岭南画派”,在当时国内艺术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20世纪初享誉画坛的广东美术家多有留洋归国的经历,李铁夫是留学美国,高剑父留学日本,林风眠留学法国,一方面,他们带着固有的东方美学底蕴;另一方面,他们的艺术深受国外艺术思潮的冲击与影响,所谓中西兼容,不过是在一个个艺术家个体身上,水到渠成地实现内外融合而已。
……
在艺术上,高剑父打出“折中中西”旗帜,是岭南近代艺术思潮对于西方态度最为坦率的表达。从艺术风格的源头来看,高剑父的“中”来自两居的师传,两居的撞水撞粉给了高剑父独特的技法作为表达手段。而高剑父的“西”来自日本,李伟铭在《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20世纪前半期广东绘画一斑》一文中指出,“在绘画上,二高早年于日画靠近竹内栖凤,陈氏则深受山元春举、望月金凤的启发”。
“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在日本学习绘画期间受维新派和同盟会的影响,进而推动着其绘画思想的变革。1912年,高剑父、高奇峰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则体现了二高在政治理想前提下的艺术追求,陈树人在《真相画报》连载《新画法》,输进新知,提倡美育,都是受到民国初政治与社会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
关于岭南画派“融合中西”绘画思想的体现,有学者概括为:以倡导美术革新、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中中西、融汇古今为道路;以形神兼备、雅俗共赏为理想;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特色。事实上,岭南画派“融合中西”绘画思想体现了中国画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将要进行的现代转型。
不过,客观地看待20世纪初由美术家主导的艺术进化,抽离了时代赋予的政治使命,所谓“新”“旧”之间孰是孰非?应该又有不同的答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画坛的“方黄之争”,主角是岭南画派的方人定和国画研究会的黄般若,这是一场关于国画的“新”“旧”问题的论争,大家都急于披上“新”装,其实质还是没有摆脱进化史观的影响。
随着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人们往往对于新旧的地位差异产生误读,认为“新”就是“前进”和“发展”,“进化”就等于“进步”,进化论下的中国现代美术,在20世纪初叶,相对简便地以西方美术发展历程作为前进的参照系,“岭南画派”尚且能兼顾本土文化体系的差异,因此,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学习价值。
——《折中中西的艺术家》
作者|李沁 徐佩雯
编辑|周笛 徐佩雯
统筹|郭珊
图片|花城出版社 部分来自网络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