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大学教授黄军甫:美国优先与大国责任

2016年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开合,俯仰百变。中东的难民潮,遍布全球的恐怖袭击,俄罗斯的东征西讨、好勇斗狠,土耳其的再穆斯林化,欧洲反建制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英国的脱欧公投等等事件渐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所有令人惊叹的事件中,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胜出及大选前后的出格言行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特朗普横空出世时间不长,但言行已搅动了世界舆论,而且大有颠覆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美国的外交理念和基本价值之势。特朗普众多言行看似没有章法,但实质上存在内在逻辑。仔细分析发现,特朗普所有言行的起点乃是所谓的“美国优先”。他在一次演说中公开讲:“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界免受他国蹂躏,他们生产本该我们生产的商品,偷走了我们的公司,毁掉了我们的工作机会。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还有:“我们将遵循两个简单的原则:买美国货和雇美国人。”
“美国优先”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未来内外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实现所谓的“让美国再伟大”。对国内少数族群和妇女的歧视,对平权运动以来“分配正义”原则的攻击,蔑视美国基本价值,煽动民粹借以挑战既定政治秩序。贸易保护主义的喧嚣,以及禁穆令和拒绝合法难民入境等都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能否达到它的预期目标,我们不感兴趣,它对世界秩序的冲击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无法预料。我们在此考问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的联系愈益密切的当下,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强国的美国总统,他所提出的这一国策正当性何在?

固然,全球政府和大同世界的目标只是一种乌托邦的今天,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分立是合乎理性的。国家的存在,一国范围内的民众关心自己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当政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内外政策都是合理的。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所言:“无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个社会边界的划定有多么的任意,但一个人民的政府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作为人民的有效代理人,对自己的领土、人口规模以及土地环境的完整性负起责任。”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是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没有阶级、因而也没有国家的全球范围内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断言,在无差别的理想社会到来以前,劳动阶级争取解放的形式首先是民族的,他们的斗争舞台是国内。因而一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合意的。正是如此,特朗普抛出他的“美国优先论”后,东西方虽然隐隐感觉不是滋味,但却很少有人给予令人信服的反驳,甚至一些国内学者私下里或自媒体上对该理念表示理解甚至欣赏。
事实上,特朗普以怨妇式的口吻,所表达的“美国优先”理念的正当性,是经不起追问的,更经受不住通行的国际正义原则的道德拷问。
众所周知,当下的国际秩序及全球治理机制萌芽于二战后期,形成于冷战期间。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联合国的架构及运作模式,都是由美国主导下形成的。虽然它在止息人类纷争,增进合作和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是强权政治和大国争斗的产物。就程序正义而言,它在起点上就是不公正的。平等尊重各民族、各国家的基本权利在康德看来是人类和平的前提。这一前提不是从经验事实中导出,而是实践理性范畴中的道德义务,绝对命令。不然,人类只能停留在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
所以,为了走出丛林法则统摄的世界,人类必须通过契约建构秩序。世界秩序如果是正义的,那么它的法则的制定必须首先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对此,规则制定者事先必须忘掉身份,用罗尔斯的话说,它们必须被置于无知之幕之后,且不能求助于某些宗教、道德学说所宣扬的“善说”。用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的理念讲必须“权利优先于善”。这样,“ 一个国家中的对外的(合法的)平等,也就是国家公民之间的那样一种关系,根据那种关系没有人可以合法地约束另一个人而又不自己同时也要服从那种以同样的方式反过来也能够约束自己的法律。这样,各方参与制定的法则才是公平的”。
然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型构是美国主导的,该秩序的法则是众多国家“不在场”的情势下制定的,规则的内容凸显的是“美国价值”、“西方精神”。所以,战后的国际秩序无论是起点、规则还是过程都充满着不正义。在世界经济领域,美元的霸权地位、对世界商品定价权的掌控、对国际贸易机制的操纵等,都是国际秩序不正义的体现。而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更是通过把持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以实现自身的利益。
事实上,在建立联合国的动议刚刚提出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对到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讲:联合国中包括美国、英国、苏联在内的几个大国(也就是后来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未来的世界警察。当然,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后来充当世界警察的国家只有美国。借助于这一“合法”身份,以“正义”之师的名号,美国人在全球横冲直撞,为所欲为。不仅以违背战后秩序为借口出兵朝鲜半岛、伊拉克,还以反恐及维护人权为名介入索马里、利比亚等国的内部冲突,甚至纯粹基于自身地缘政治、经济的利益而颠覆了智利阿连德、危地马拉阿本斯、伊朗摩萨德等合法的政权。
没有程序正义就不会有实质正义。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以后,借助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全球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的数量显著下降,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全球11亿人脱离赤贫”。但由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世界的发展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有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国际秩序的不正义不仅加剧了不平等,还加剧了国际资本的野蛮化及贪婪性,从而使地球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使人类生存环境被不断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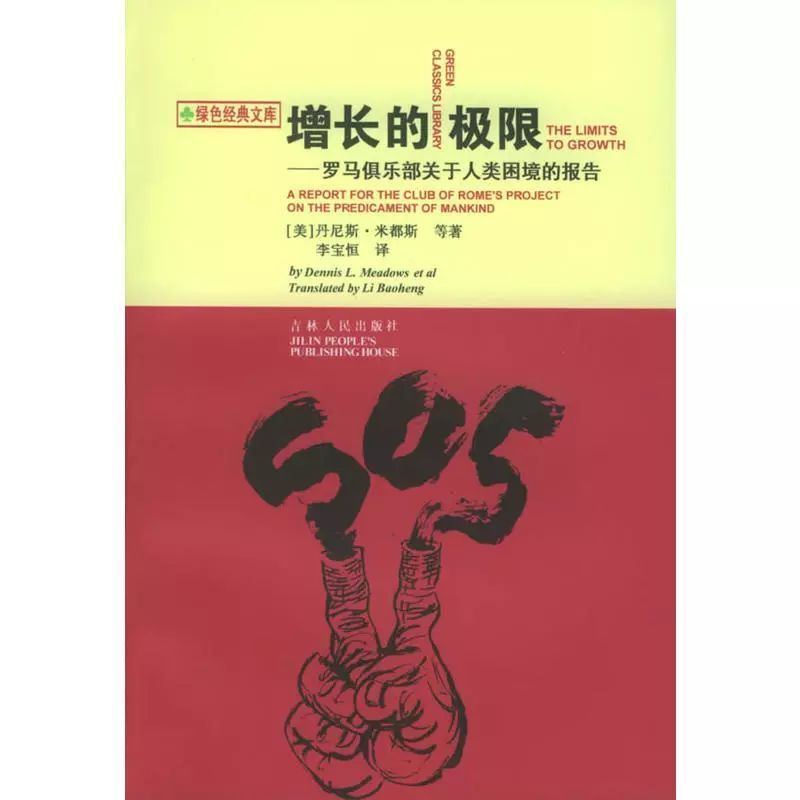
它的直接后果便是《增长的极限》一书所描述的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该书为了使其论点更明晰,提出了“生态足迹”这一反映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概念。所谓生态足迹是指“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粮食、饲料、鱼类和城市用地)和吸收排放(二氧化碳)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按照这一指标,2004年的时候,人类资源的利用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20%。就此而论,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显然已陷入困境。困境的出现不仅仅源自“过冲”性的发展,更多的源自发展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据美国注册的全球生态足迹网(GFN)新近披露的数据,目前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为2.7公顷(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而美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为9.5公顷。据该网站计算,“按美国人均足迹计算,我们需要5个地球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
既定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中,美国占尽先机,处处优先。它必须对当下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负主要责任。
《增长的极限》的作者曾经提醒世人,为了避免“增长极限”的到来,甚至现有秩序的“崩溃”,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人类必须提高这个世界上穷人的消费水平,同时减少人类总的生态足迹。因此必须有技术进步、个人的转变以及长期的视野;必须要有超越政治疆界的更高的尊重、关切和分享”。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国际规则、治理机制的合理、公正,它构成国际秩序的背景正义。背景正义仰赖各民族、各国家、各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仰赖对话基础上的重叠共识。只有背景正义才能保障《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及“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在背景正义存在的前提下,正义的理念和原则要求国际社会中“组织有序”的人民担负援助因历史的偶然性而“负担沉重的国家”的义务。“组织有序”的人民还必须尊重“负担沉重的人民”的移民权和康德所言的“访问权”。 康德强调,“这种权利是属于人人都有的”,而“地球表面作为一个球面是不可能无限驱散他们的,而是最终必须使他们彼此互相容忍,而且本来就没有任何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在地球上的某一块地方生存”。
显然,国际正义的实现无论是就形式还是内容,都需要罗尔斯所说的“组织有序”的国家,尤其是大国的道义担当。“这是因为支持这些原则的理由要求有极大的远见,并且经常会出现反对这些远见卓识的强大激情。但说服公众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原则的巨大重要性,正是政治家的责任”。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及基于这一基本理念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歧视、限穆令,以及禁止难民入境等言行,都与国际正义理念格格不入,是曾经被“政治正确”的表象遮蔽的强权政治、种族主义及西方中心论的公开表达。它不仅难以借此“让美国再伟大”,而且很可能使美国及世界的问题更复杂。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讲,每个人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个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所彰显的推动历史的力量,最终形成合力,从而决定历史进程的方向。显然,重大的历史人物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无疑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担负着更大的责任。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每个民族都在各自既定的文化传承里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世界的历史。而世界历史的合理发展则需要大国承担较大的责任。诚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所说:“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
征文啦!

“初心耀征程 • 改革开放再出发”征文活动启事。点击查看详情》》
统筹丨戎明迈
编辑丨李梦醒 影子
校对丨华成民
来源丨解放日报、探索与争鸣微公号

 快来抢沙发
快来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