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许渊冲回应“抄袭”争议:我英文怎么不行?

许渊冲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
许渊冲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主动提起黄少政质疑其中诗英译成就一事,“他说我把中国一千所外语院校的英文教授全部骗到,以致骗到中国电视台,骗到国际译联!”“把天下人都说成笨蛋啊,一个人怎么可以骗得所有人?”
”
许渊冲住在北京大学畅春园的70平米单元房。每天,他准时收看中央四台的《海峡两岸》《中国新闻》《今日关注》,“看得可认真。”他的妻子照君说。接着他将工作到夜里三点,晚间骑车到颐和园,当休息;早上八九点起床,做完西南联大时期学的那套马约翰操,便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雷打不动,一天一页,最近刚翻完第十三本。
1939年翻译林徽因诗《别丢掉》算许渊冲翻译生涯的开端。1980年代后,他进入高产期,从《诗经》《楚辞》译到明清作品,翻译理论逐渐成形:《翻译的艺术》(1984)阐释了“三美论(音美、形美、意美)”“优势论”,《中诗英韵探胜》(1992)用自己的译论对比分析中外译作,1999年《译学要敢为天下先》一文回顾了严复、鲁迅、郭沫若、林语堂、朱光潜、傅雷、钱钟书等人的译论,总结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十字理论。
老师钱钟书称他的译诗“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顾毓琇评价他“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2014年,许渊冲获得国际译联“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之后,他陆续参加《朗读者》等节目,获得更高的关注度,也变得“忙一点,累一点”,他说。“我累”——照君接话,“这一切的一切,秘书、通讯员、保姆,都我一个人当。”最夸张的一天,她接过16个媒体来电。
中央十台来拍了许渊冲的传记片;BBC最近也每周来家里一次,从早到晚,拍摄许渊冲日常生活。去年,山西大同大学成立了许渊冲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院,今年初举办了首届“许渊冲翻译大赛”。11月即将到来的西南联大80周年庆,他也受邀参加。
最近,许渊冲的规律生活被打断。
学者黄少政(退休前为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七八月在网上连发长文,以激烈言辞质疑许渊冲的中诗英译成就。黄少政称,他从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许渊冲译作,九十年代还慕名登门过,但讨教体验不太好:“他家里一个小书架上都是自己的书,我想,他不需要读别人的书吗?”今年,他写了一本《中国翻译十批判》,探讨中国翻译界十个名人,其中许的部分主要关注英文写作,“他(许渊冲)的句法和词法的复杂性都太低了,理论上是‘中介语’,不及格的英文。写完文章我顺便看了他译的几首诗,非常巧,正好是译陶渊明,其中有一个人是‘罗兰’,我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译唐诗的外国人。后来追查出来,方重先生出过翻译陶渊明的诗集,罗兰是他求学时的英文名。他们的诗一对比就吓一跳,一行一行地抄,只是最后换一个字。后来我查他的重版书,又把翻译做了改动。”
迄今为止,他已发表四篇“阶段性打假成果”,共约七万字,指向许的英语水平“不够格”,词法、句法简单;译诗“破韵破句破体”;有抄袭前人弗莱彻、方重等人之嫌。“许译凭押韵译唐诗走红就是一个国际笑话。这个上世纪初小心翼翼试译《毛泽东诗词》的中诗英译门口的陌生人,终于在他年届九旬时凭着押住尾韵就敢译中诗,并获得国际译联的‘北极光’大奖,完成了向无视英诗传统格律,连抄袭带三破(破韵破句破体式)的野蛮人的华丽蜕变。”黄少政在文中写道。
“你去查一下外国亚马逊网,他的书没有一本在售。他的英文非常垃圾的,就是有几个金句把别人都骗了。我希望国外汉学家能够介入,很容易断定他的水平。”黄少政在电话采访里说,文章发布后,有不少人私下对他表示支持,但他“不能说得太多”。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助理研究员叶丽贤曾仔细阅读过不下百首许渊冲的英语译诗,并将之与其他国内外知名译者译作比照,“无可否认的是,前人的译作是许先生在执笔翻译时常会借助和化用的资源。我的总体印象是,他的译作可能并不总是最出色的,却也绝不是佳作中最平庸的。他在国外知名度更高的是他的翻译实践。有一些百科全书称他是中国国内目前尚存于世的最出色的古典文学译者,这么说倒也不夸张。”
“押住尾韵就敢译中诗”在叶丽贤看来属不当之论。他认为,黄少政指出许译诗中的大量低级语法错误都是许为了迁就押韵或保证每行诗的音节数所导致的“破格”现象,并不代表他不知道相关语法点,或者在写英文文章时也会犯这类错误。“许先生的译诗集曾在企鹅出版社出版过,如果他译出来的只是押了韵的打油诗,这家出版过大量经典文学版本的公司大概是不会选择许先生的译本的。”
“他的英语写作水平在国内应该算是顶尖的,但我认为他确实在‘破格’使用英语这一块,过于大胆了些。与其它一些欧洲语言(如意大利语)相比,英语词尾变化比较多,也就是说,很多词是找不到太多以同样音节结尾的词的。如果在翻译古典诗词时过于坚持中文原诗的押韵模式,就可能导致以韵害意的问题。许先生翻译的诗词常被人指摘的就是这一点。”叶丽贤说。
叶表示,他和周围一些从事文学翻译的学者都关注了黄少政的批评。“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不过有一点大家还是认同的:黄少政的文章过于主观武断,有例证,但不充分,未达到学术文章的基本严谨要求,不足为信。但他的文章还是有一个积极效果,就是提醒广大读者,切莫盲目崇拜大师的封号,让我们在读他们作品时,多点独立的判断。”
黄少政表示,他可能11月份到北京,到北大学术委员会投诉,检举材料已经准备好。“我是独立翻译学者,独立承担责任。以前有人和他(许渊冲)商榷译法,我是第一个上来说,你抄袭了,你的问题性质不同了。”
许渊冲和妻子照君都不上网,前不久才由学生告知此事。观察者网7月的报道《黄少政:许渊冲诸多诗为抄袭之作》以及黄少政的原文《许渊冲如何抄袭中诗英译的名家弗莱彻,韦利和方重?》被打印出来,现在放在他工作的房间。谈话间,照君连连摇头,“许先生是有名的风骨纯真,”她竖起大拇指,“有名的狂人啊,宁愿死也不会抄人家的!别人值得我抄吗?(黄少政)拿这种话伤人家。我真是十分不了解这个人,也太差劲了!为他生气太划不来了,甚至值不得跟他对阵。我们跟方重关系很好的;我儿子也是上外 [ 方重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任职 ] 毕业。”
许渊冲接受采访时亦主动提起此事,“从没有这样批评的,说我抄袭、英文蹩脚,常识都没有了!这太坏了!他说我把中国一千所外语院校的英文教授全部骗到,以致骗到中国电视台,骗到国际译联!”采访中许渊冲反复提起这些“骗”,“把天下人都说成笨蛋啊,一个人怎么可以骗得所有人?”他说得有些激动,然后笑了,“也有点气的。”
作为译者,许渊冲自觉担负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今年9月1日,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上,他向台下的孩子们介绍翻译的“三美”,最后说:“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使我们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发展。”在他家,他翻出自己的文章《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给我看。文章里,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实现“中国文化梦”。对文学翻译工作者而言,“一方面要把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另一方面又要把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译成外文,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1949年,西南联大校友会成员在巴黎欢迎到访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右二),左二为许渊冲
《归园田居》是方重让我改的
◇◆◇
人物周刊:你对黄少政有印象吗?
许渊冲:我见过他一次,他是辜正坤带来的。但只谈了一个小时,谈的内容也不大记得。我对他(黄)只了解这个文章。他学历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他是青海师范大学的副教授,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这对我简直是骂嘛!
第一个例子就是我抄方重的。他的英文名字是Roland C. Feng,黄少政的说法是“美国人罗兰”,表示他本来根本就不了解方重是什么人。方重是我老师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教书,1980年出版了陶渊明诗集。因为我翻译诗比较多了,他请我评论,我就写了一篇评论。我认为他翻得不错,但根据“三美”的原则,我跟方重说,翻得好,要是加上音美、形美原则就更好了。
人物周刊:这篇文章你现在还保留在家里?
许渊冲:对,我后来登在《翻译的艺术》里。(到书架找出该书,翻出)“《谈方重的翻译》,”你看,“总而言之,方重的陶渊明诗翻得很好,令人赞赏。但是,如果能再锦上添花,加上译文的音美和形美,那就可以和翻译史上的《鲁拜集》比美了。”
人物周刊:方重怎么评论?
许渊冲:方重同意。他问我,怎么改更好?我就给他改,就是他(黄少政)举的例子。我改得很好,方重还在上海政协食堂请我吃饭。怎么会是抄袭?你不了解情况怎么能乱说呢?还好文章留下来了,这事上海外国语学院1980年《外国语》第六期有报道。
方重翻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Beneath the southern hills I sow my beans,他最后用的复数。Their shoots are lost among the rank grass没有韵。我建议改成这样:Beneath the southern hills I sow my bean,我把s取消了,押韵。下句Bean shoots are lost among the rank grass green我加了green,和bean押韵了。这是抄袭吗?是他自己要我提意见。我还改得更好啦,不但有意美还有音美啦。所以他自己都说,“一字之师”。这个例子就可以证明了。
我的翻译胜过弗莱彻、韦利
◇◆◇
人物周刊:他还提到英国的弗莱彻(W.J.B.弗莱彻,唐诗英译译者)。
许渊冲:黄少政说的第二首更妙,《登高》。这是我的名译啊!(拿出书架上的《中诗英韵探胜》)看《登高》,弗莱彻翻译的第一句是The wind so fresh, the sky so high,我的是The wind so swift and sky so wide。我“抄”了两个字,wind,sky,这算抄吗?
下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两句我翻得很对的。弗莱彻的是Through endless space with rustling sound.The falling leaves are whirled around.Beyond my ken a yeasty sea.The Yangtze’s waves are rolling free.但没有“三美”啊。我怎么可能抄他的?有常识的一看就(知道),我比他不知道好(多少)。
余光中在香港一次谈话的时候说,这是不可译的。为什么呢?“无边”对“不尽”,“落”和“萧萧”都是“草”字头,下句“江”“滚滚”都是三点水偏旁。既有意美,又有音美形美,怎么转达?《明报》登了余的说法,杨振宁拿给我看,问我意见怎么样,我就把我翻的给杨振宁看,“三美”都翻出来了: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boundless对endless,shed和shower都是sh-,river和roll都是r-。“萧萧”翻译成shower by shower,这不是我的,是我老师卞之琳翻的。也是我问他,这翻得很好啊,应该对下联啊!他说,没有办法,你试试看。我就翻了hour after hour,shower和hour还押韵,就是好。内容上看,也不是乱加的,“不尽长江”有时间和空间的不尽,空间的不尽是endless,时间也是不尽的,就是后面的hour after hour。杨振宁把我翻译的寄给《明报》,他们登了,原稿我没有,但可以查到。企鹅出版社出了我的翻译,就用这个。
这两个例子够了吧?为黄少政这个牺牲我的翻译时间,不值得。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韦利的翻译?
许渊冲:我写过一篇《诗词英译可以走向世界》(《英语世界》,2015),说我胜过韦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韦利翻成learn,“习”翻成repeat,“说”翻译成pleasure。“学习了又复习,是很快乐的事。”对学生说可以,但孔子这话是对君子说的,就不行了。所以我把“学”翻成acknowledge,是指“得到学问”。得到知识而且把知识付之实践,put into practice。“说”我翻成delight,是说精神上的愉悦。“学”是真,“习”是善,“说”是美,孔子一句话里包括三个层次,韦利翻译里一点都没有。这个例子说明我比韦利强多少啊。怎么能说我抄韦利?我远高于他了。我说英美人英文再好,对中文理解只有50分,我的中文理解能力有八九十分,英文表达能力也八九十分就够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到底是洋为中用还是崇洋媚外?我是洋为中用。
还有《关雎》。“关关雎鸠”他翻译成Fair,fair,cry the ospreys。对“鸠”的解释有三种,水鸟、白鹭、斑鸠。哪种对?要看本领了。韦利翻译成“水鸟”,水鸟哪有fair fair(“美啊,美啊”)叫的?所以翻得不好。斑鸠叫声是“咕咕”,“咕咕雎鸠”,声音不响亮,加个-an就变成“关”,响亮得多。中国两千五百年前就知道用元音显示这个。我翻译的是By riverside are cooing.A pair of turtledoves.这个译文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人是懂的。我拿大奖是无愧于心的。我在英美都出版了,评价都很高啊,看到的人不一定多,外国对中国这些感兴趣的人有几个啊?
人物周刊:你了解出版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吗?
许渊冲:学生跟我反映过,知道的不多。(影响力)只能是华文界了,在美国你能希望怎么样啊?我们的书在美国想很怎么样是很难,但是在华人中间是可以(传播)的。对中国没兴趣怎么会看我们的东西?没办法,这只能慢慢来,等国家强盛——现在好多了,我们的留学生多了。就我刚才举的例子,根据他们(弗莱彻、韦利)翻的第一句话,谁看?我的翻译,道理多深啊。
拿国际大奖实至名归
◇◆◇
人物周刊:这就说到了大奖问题,2014年国际译联把“北极光”奖颁给你。
许渊冲:他说我英文不行。我英文怎么不行?一百六十多本书怎么出来的?他说我“把中国一千所外语院校的英文教授全部骗到,以致骗到中国电视台,骗到国际译联给他颁发最高的‘北极光’奖项!”一个人有这样大的本事啊?还有这些人都是饭桶啊,看不出来?他怎么有资格说这个话?
我就说一个,《诗经》里的千古丽句,国际译联给我文学翻译奖的根据之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八句表达了中国古代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打仗。我翻译的是: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
Long,long the way;
Hard,hard the day.
Hunger and thirst;
Press me the worst.
My grief o’er flows.
Who knows? Who knows?
第一句“杨柳流泪”,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翻的。杨宪益翻的fresh and green,什么意思?到最后一句“我的悲哀像水一样流满了一条江河,谁知道我的悲哀呢?”我都只用四个字啊!又要把内容传达,又押韵,谈何容易啊?你说还有比我更能拿世界大奖的吗?
他有些话都说得不成话的,很那个的,简直是骂嘛!我说自己“不是院士胜院士”,他不赞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时候中国工程院院院长是朱光亚,要每个院士都放一本我翻译的唐诗,作为他们对外交流使用。我不能说“胜院士”吗?这书是院长要每个院士读的。
还有“三美”,这是鲁迅提出来的,还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三美”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的,你反对这个,不是反对我。所以我说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是“要用‘三美’这个办法走向世界”。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公号
文 / 实习记者 张宇欣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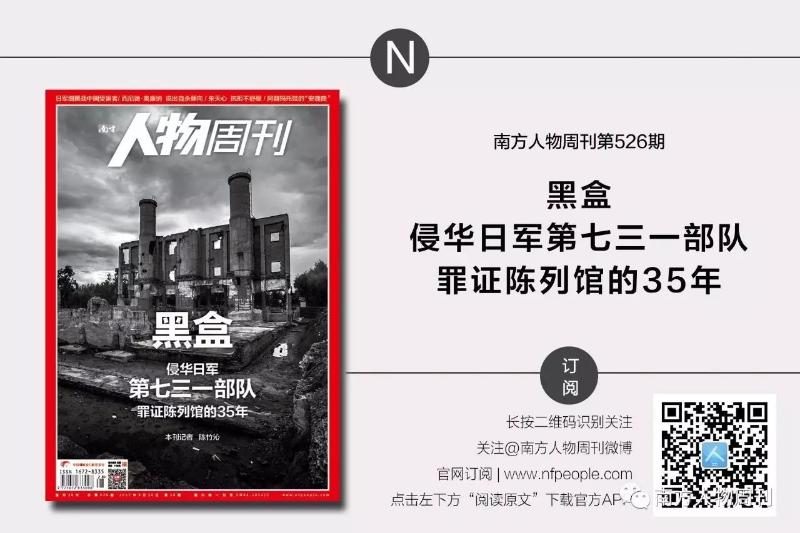
 快来抢沙发
快来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