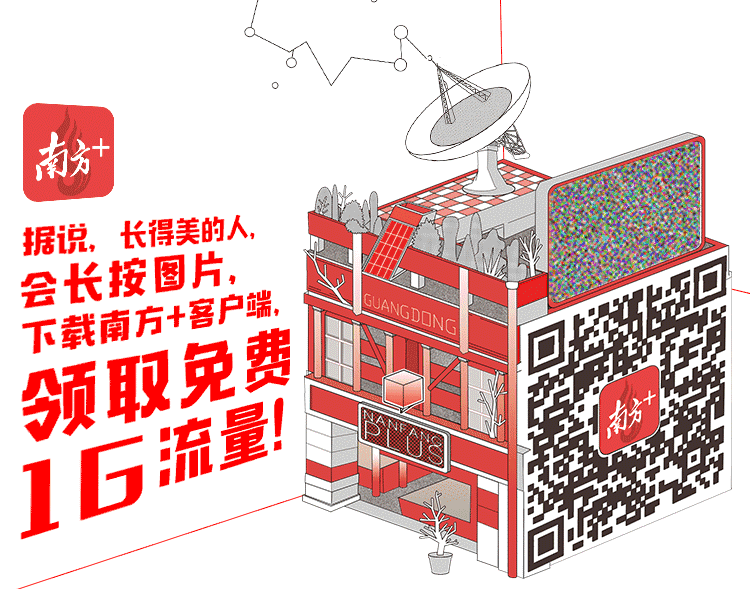深度|直面“惠州最穷的地方”——惠东马山村如何走出“山路十八弯”?
惠州观察 记者 徐乐乐 2016-11-07 13:44
在茶园里,村民曹日高(左一)看着已露尖的茶叶一脸喜悦。徐乐乐 摄
惠州最穷的地方在哪里?
当我们试图向市县两级扶贫部门寻找答案时,提及最多的便是马山村。
驱车从惠东县城出发,90多公里的路程大多是在大山深处蜿蜒攀爬,一直到西枝江上游,才看见袅袅炊烟从山头飘起。马山村就镶嵌在青山绿水环绕的乌禽嶂山腰上。
这里地处惠东县宝口镇东北部,属于偏远山区,也是革命老区。3年前,村里户籍人口尽管有4000人之多,但常住人口只剩900多人,其中近400人属于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接近10%,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是上一轮扶贫开发中的省级贫困村。惠州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从贫困发生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来讲,马山村是当年全市最穷的山村。”
当驻村干部曾柏军在山里绕了3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村里时,他的第一感受是“心都凉了”——路走不通,车进不去,没下雨时都是泥巴路,“扶贫的路怎么走?”
直到2013年,第二轮扶贫开发“双到”工作启动。就在这片尚处贫穷的红色土地上,一场为期3年的精准扶贫攻坚战也正式打响。3年来,马山村民发扬红色革命老区顽强拼搏的精神,通过扶贫、扶智、扶志,积极展开反贫困斗争,一跃成为全市精准扶贫的典范。
通山路
日求三餐夜求一宿,
卖袋稻谷要走几十公里山路
“夜半山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呦盼春风。若要盼得呦红军来,岭上开遍呦映山红……”10月底的一个午后,一位壮汉穿梭在茶林中,低声哼着这首《映山红》,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
这壮汉便是马山村党支部书记钟少文。山歌哼出了革命老区的情,也哼出了马山村脱贫致富的景。满山都是飘香的茶树、山花、甘薯,他抓一把茶苗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开了春就是钱咧!”
放在3年前,钟少文想都不敢想。“山旮旯,村民种点什么,想卖都卖不出去,有把力气的人都跑出去打工,靠什么致富?”
这就是马山村的苦。自建村以来,几乎与外界隔绝,想富也只能望山兴叹。惠州市质监局在成为扶贫挂点单位时对马山村进行过调研分析,结论是: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信息不畅,且适宜的耕地有限,易受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村民增收致富难!
钟少文至今还记得,他2008年刚进入村委工作时,一位低保户因为住不了漏风漏雨的泥瓦房,找村委帮忙组织募捐盖新房。本来按照当地习俗,选了黄道吉日要给工人发个红包,但这位低保户连十几块钱的红包都拿不出。“看到村民穷成那样,心里不是滋味。”
马山村穷,首先穷在交通上。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民外出还要靠水路,村民在山上砍下木材,然后捆在一起铺成木排,人就在上面搭上棚子,顺着西枝江飘到外地去卖,来回耗时一个多月。老一辈人扛一袋稻谷到最近的圩镇卖,也要走几十公里的山路,往往天不亮出发,第二天才能回来。
后来,马山村到邻近的高潭镇通了路,再到2005年,县道进了村,实现了硬底化,马山村这才渐渐走出了大山。
“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是当地流传的一句话,道出了马山村几辈人追求温饱的梦想。村民接着感叹道:“可就是绕不出那山路十八弯!”
不过,对于驻村3年的扶贫干部曾柏军来说,马山村又何止十八弯,他每次从市区开车到村里都要3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耗在弯曲回肠的山路上,“驻村时刚好买了新车,3年下来跑了8万多公里山路,刚开始还真心疼。”
“一二三,推……”“一二三,再推……”驻村不到一个月,曾柏军已有4次从泥浆中把车推出来。县道是早已进了村,但村道仍然泥泞不堪,尤其到雨季,自然村之间更无法通行。
山区要脱贫,首先要开路。自2013年启动扶贫工作开始,扶贫挂点单位惠州市质监局便把“第一刀”对准了基础设施建设。疏通泥石流损毁的村道60多处,修复村道30多公里,对2公里村道实施硬底化改造,实现了村委到300人以上自然村硬底化全覆盖,还有20多公里村道正在按计划实施硬底化改造中……
今年8月,挂职结束的曾柏军再次回到了马山村,看着进出村里的车多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又重走了当年的泥泞路,然后发了一条微信:3年前,感慨扶贫的路不好走,如今马山脱贫了,当年下雨必打滑的村道也都硬底化了,这3年是马山变化最大的3年,携手共建幸福新马山,我们做到了!
抗洪灾灾后重建过冬暖,丰衣足食迎新年
“洪灾无情人有情,党员干部做脊梁,喜庆洋洋入新居,炮竹声声进新房。”走进在马山村大布村小组广场,一栋栋橘红砖墙的民居熠熠生辉,门口的对联格外醒目。
79岁的黄显富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晒起了太阳。老人口齿已不太清楚,着急地指着门口外墙示意我们看。
墙上钉着一张铁牌,上面记录着“历史洪痕108.07米,发生时间:2013年8月16日”。对所有马山人来说,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一天,也是他们遭遇天灾又重新站起来的一天。
2013年8月16日,台风“尤特”袭击了惠东县。宝口镇、高潭镇一带成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当地降雨量一度达到1100毫米,为惠州市乡镇气象最高纪录,百年一遇。马山村由于地势低洼,成为雨水汇集点,村里大部分农田受浸,断水断电断通信,多条出路被堵,成为与外界失去隔绝的“孤岛”。
“当晚2点多,我给老婆打电话说,不回来了,可能也回不来了。”回忆当时的场景,村干部张胜源脸上的肌肉又开始抖动起来。8月15日他就接到县里通知开会,但走到半路路就被洪水冲断了,赶紧跑回来转移群众。
16日晚,洪水暴涨,山上黄泥不断下泻,钟少文等村干部带上大型手电筒和防空报警器来到河边,拉响防空报警器,并用手电筒示意村民往山上高处转移。村民赖连芳的家就建在山坡上,见村干部过来动员转移,他一脸不悦:“住了半辈子,啥风雨没见着,倒不了!”
村干部也顾不了那么多,拉起赖连芳就往外跑,谁知他们前脚踏出门,后脚泥石流就把房子“轰”的一声压塌了。赖连芳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手紧紧拽着村干部。
暴雨一直到17日晚上12点才停,这时的曾柏军正在医院的产房陪护妻子,因为妻子马上临盆了。得知马山村受灾,曾柏军心里七上八下。他一边陪产,一边拨打6位村干部电话,但由于通信中断,一直未能接通。女儿18日凌晨1点降生了,此时,马山的大暴雨也恰巧停了下来。
暴雨过后,曾柏军中断了陪产假,马上赶到马山村参与救灾和重建。经灾后核查,马山村上百间房屋在洪灾中受损,仅大布村小组就有29户房屋倒塌,其中全倒户19户,上千人无家可归,许多本已贫困不堪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面对马山村被洪水袭击倒塌的泥砖房,政府及各界爱心人士纷纷驰援。政府给每户全倒户6万元的建房补助,属低保户的再补助1万元。
惠州市慈善总会港澳基金会筹集捐款500多万元捐给惠东灾区,并在马山村大布村小组为19户全到户建起了“幸福新居”示范点。同时,马山村敬老院也拔地而起,提供给村里12户五保户居住。
春节前,受灾群众全部搬进了新居。2014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带队看望受灾群众,刚搬进新居的村民唐百坤特意在门口贴上了春联:灾后重建过冬暖,丰衣足食迎新年。握着干部的手,他刚说了一声“谢谢”就哽咽说不出话来。
村民说,贫穷的马山人,顽强的马山人,经历洪灾的马山人必将再次站起来。
致富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再穷的马山人,也有致富的强烈愿望。再有力度的扶贫,也不如发动村民进行开发式扶贫。
47岁的曹日高不想穷,也不服穷。他尝过穷的滋味,“顿顿喝粥就番薯,吃不饱。”
曹日高暗暗下了决心,人在,力气在,不信富不起来。种稻、种菜、种瓜,啥都种,还下大本钱买了机械设备,一天到晚,他都守在那十几亩地里。
可几年下来,曹日高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仔细一盘算,除去人工、肥料、设备费用,一亩田200块都赚不到。再转眼看看这个家,老婆离家出走了,老母亲患病在床,两个孩子马上要上高年级了。
曹日高心里铆着劲,“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铆着劲的人还有曾柏军,挂职村第一书记几个月以来,他总感觉无从下手。马山村山多地少,土壤薄弱,不适合种庄稼。他不想拍脑袋,也不想直接把扶贫款发给村民了事,于是就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建档立卡,着重发挥村“两委”推动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把村“两委”班子打造成一支永不撤离的扶贫工作组,带领村干部们仔细调研。
扶贫要解急难,更要看长远。曾柏军发现,马山村有种甘薯的传统,少则三五分,多则一两亩,但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和销售渠道,村民几乎挣不了钱。经过多次论证,曾柏军决定采取长短结合的产业扶贫办法。先投钱支持贫困户种植甘薯增收,然后扩大面积,同时积极联系惠东县甘香农贸有限公司收购加工,形成统一生产模式,不少贫困户很快尝到甜头。
精准扶贫不仅是扶贫到户到人,还要结合当地实际。曾柏军发现周边村有些散户种植的茶叶一斤可卖到800元,这一下子打开了他的思路。山地适合种茶、种竹,并且生长快、产量高、收益大,马山村再适合不过了。
但刚开始,村民不相信。惠州市质监局作为扶贫单位就先建了马山茶园示范点,提供30000株茶苗免费给贫困户种植,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及贫困户带来3.5万元的收入,为每户贫困户增收1万元以上。
种下的是树苗,收获的却是村民致富的信心。曾柏军跑到曹日高的家里,两人一合计,田不好种,咱种茶。在村委帮助下,曹日高腾了3亩地,种下了茶苗,说死活都要再试一回。
一年又一年,曹日高盼茶香盼得切。一个下午,他带着我们来到茶园,一片绿油油的茶叶已开始露尖儿。前几天,曹日高提前摘了7斤,每斤卖500元,“刚开始不敢卖贵,明年开了春,每斤可以卖到800元,这一下子就有好几万的收入咧!”
在示范点和部分农户的带动下,马山村的上百家农户的种茶热情一下子给点燃了起来。有的种茶,有的种竹,少则几亩,多则几十亩。他们联合兴家茶叶专业合作社,挂上了“兴家名茶”的品牌,建立起了兴家名茶产业培育基地。
甘薯、茶叶、竹子……如今,马山村的产业真正走上正轨,村集体收入从2012年的2.8万多元一下子飙升到2015年的17.4万元,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从3312元提高到10322元。
在巡茶园时,曹日高一边嚼着茶叶,一边抱怨村委当初没让他多种几亩。曾柏军笑着问:“这茶啥味儿?”
曹日高嚼了嚼,“苦的呗”,他又嚼了嚼,然后呵呵一笑,“多嚼会儿就成甘甜的喽!”
求学梦马山村的穷,马山人的梦,马山的孩子马跃龙腾
汩汩西枝江水路过乌禽嶂南麓奔流而下,绕着马山向西南方向逶迤100多公里,在惠州繁华的市区汇入了东江。
在江水绕过马山村的地方有一个山头,外形似马,马山村因此而得名。马山村一代一代的人就在这里眺望着外面繁华的世界,希望马到成功,奔腾千里。
曾钧生从小就有这个梦,但因为家里没钱供他继续读书,初中毕业就拾起了锄头。他不甘心,在家自学看书,每天练书法,后来成了村委会的文书。“对于我们山里人来书,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没有文化很难生活。”
读书,是马山人走出大山的希望,读书,是马山人反贫困的渡船。
在钟少文记忆里,教室是泥土房,课桌是破木板,到上世纪90年代,他回家看书还要点煤油灯。“要是出了个大学生,那就是马山村的特大新闻。”
曾钧生暗暗发誓,再穷再苦也不能让孩子不读书,他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了孩子们的身上。三个孩子给父亲争了气,一个考上了深圳大学,一个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还有一个在县里上高中。村里人一谈到孩子,曾钧生就成了大家口中的模范。
一个家庭改变命运要靠教育,真正的扶贫就要扶智、扶志。从一开始,曾柏军把马山村尤其是贫困子女教育问题放在首位。张相媚是贫困户的女儿,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曾柏军知道后,劝她继续读书。
在扶贫单位的帮助下,已打工一年的张相媚又回来上了惠州技师学院幼师专业,如今毕业在淡水一家幼儿园上班。“感谢扶贫干部,是教育扭转了我的命运。”
2013年帮扶以来,惠州市质监局共筹措资金4.86万元帮助17名考取大学、中职中专等院校的学生顺利就读,帮扶他们掌握一技之能,以技能改变命运。在扶贫工作中,马山村下大力气改变教学条件,目前已拥有小学和初中两所学校。
教育之计并非一日而成。一直以来,村里的学生很多上完中学就辍学外出打工,在校学生人数逐渐下降。赖显灵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的母校马山中学在2003年左右还有400多个学生,如今已经不足百人。
“山区穷,学生上学不易,老师也不愿意去,我不回去家乡的孩子更没人教。”2008年,大学毕业的赖显灵本有很多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但他还是选择回到了马山,拿起粉笔,一教就是8年。
马山村留守儿童多,赖显灵带的班有一大半还是单亲家庭。一个学生本来考上了县里美术特长班,但家里兄弟姐妹多,就没上了。“小孩特别努力,很懂事,每天早上6点多就步行到学校,放学后,别人都有父母接,她一个人还要步行回家帮家里种菜。”
赖显灵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一边苦口婆心跟学生家长做工作,一边联系免费招生的技校,最终又把这位学生送回了学校。
马山村的穷,马山人的梦,马山的孩子马跃龙腾。在马山中学,赖显灵站在讲台上教起了英语。看着学生们殷切的眼神,他说:“一辈子在家乡做老师,我愿意。”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徐乐乐
编辑|谢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