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从父辈那儿“偷”故事
 2016-08-14 20:12
2016-08-14 20:12
文|宋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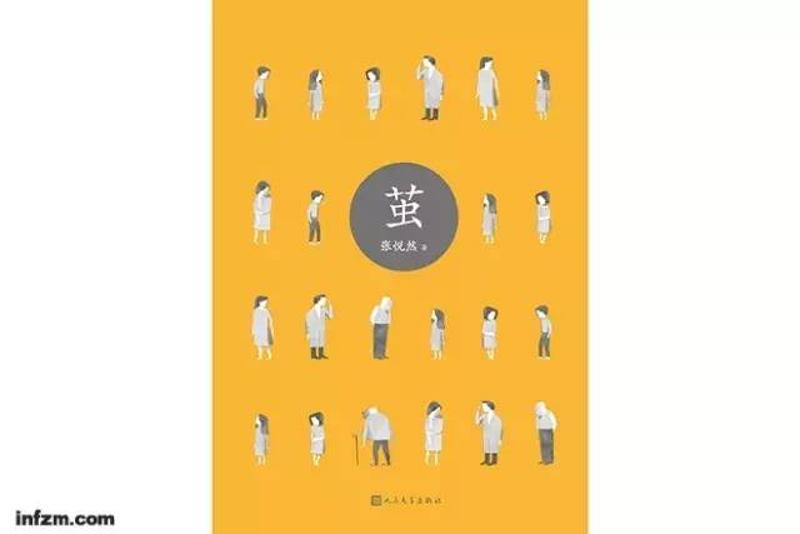
“为什么只过了十多年,我们就变得如此疲惫?”出生于1982年的作家张悦然不解。她说的是和她年龄相仿的80后。“一方面,在精神上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另一方面,肉身已经疲惫不堪,有一种中年人的状态。”
以韩寒的《三重门》为标志,80后作家在2000年左右进入市场,2004年大规模进入文坛。
那时,“韩寒、春树等作家作品还会批评一些社会现象。现在,尖锐的青春文学已经找不到了。”而三十来岁、本应富有朝气的80后,“好像失去了好奇心和斗志”。
很多80后作家已经不再写作。张悦然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开设小说鉴赏、创意写作等课。
在张悦然眼中,80后更在意个人的世界,对外界“有一种漠然和不关心”。她的小说一度也如此。
张悦然正在将自己的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改编成电影,还将亲自执导。小说里,主人公璟是位作家,自幼遭到母亲仇视:怀上她之后,母亲产生了美貌逝去的危机感。璟11岁,奶奶、父亲先后死于心脏病,母亲改嫁。她爱上继父,后来被母亲送去寄宿学校。后来继父又车祸身亡。在《人民文学》刊载时,张悦然在小说开篇有句引言:“我常常陷于无爱的恐慌中。”
2016年7月刚出版的《茧》,是张悦然的第四部长篇,主人公还是80后。书中也有灰色,人物也依然疏离、缺爱,但故事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更紧密。她想通过写这本具有“更大的主题”的小说,也更多地了解父辈。
父亲竟然也写过小说
2001年获得“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后,张悦然密集出版了一批作品。
第三部长篇小说《誓鸟》,故事背景是郑和下西洋。“我对那段历史没有个人观点,只觉得很迷人、很浪漫。”写明代历史,张悦然延续了自己一贯的风格。“把我那种抒情、华丽的辞藻推到了顶峰,看起来特别华美,又特别虚幻。”
她也尝试其他题材,但总是写着写着就“虚”了,沉湎于抒情,“感觉特别不对”。她想抛弃这种风格,“用一种更朴素的方式,去写更大的主题”。
小说《茧》就是这种尝试——80后程恭和李佳栖同在一个医科大学家属院长大。程恭的祖父遭人毒手,成了植物人,他的奶奶、父亲无助而暴躁,仇恨几乎是活下去的唯一动力。李佳栖的祖父则隐藏行凶秘密,成为名医、院士。18年后再相遇,虽有家族仇恨,两个年轻人却越走越近。
《茧》的故事是张悦然从父亲那里“偷来”的。
张悦然的祖父母都学医,父亲在医院家属院长大。13岁时,隔壁楼一位相熟的医生叔叔遭到批斗,慢慢失去行动能力,成了植物人。医生在他脑袋里发现了一枚铁钉,长度超过8厘米,凶手一直没找到。
张悦然的父亲是文学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山东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以这件往事为基础,写出第一篇小说《钉子》。小说投给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没过多久编辑来信,稿子采用,并表示赞赏。一个月后,编辑部再度来信,说小说调子太灰,没法用。再写几篇,结果也是:调子太灰,发表不了。毕业后,他留校任教,结婚,生了女儿张悦然,不再写小说。
张悦然写作后,才知道父亲也写过小说。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她很想把过去的故事写进小说。父辈、祖辈的真实遭遇,也被她编织进了小说。
张悦然小时候,母亲常带她去外公的故居——一套完好的院落,全家人曾一起住在那里。张悦然去时,那里变成了居委会。母亲告诉女儿:“以后再把这些事讲给你听。”
外公早早去世。他做过银行家,性情温和,受过批斗,有时一个人去饭馆,点一份糟熘鱼片,坐下来慢悠悠地吃。“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生活的尊严。”张悦然设想外公的心境。
动手写《茧》时,母亲已经遗忘了很多,没了怨愤,也不再着急讲往事。
祖父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偶尔还能回忆起一点往事。他坚称自己与孙立人将军合过影,虽然找不到照片,但引以为荣。他在齐鲁大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入缅作战,负责翻译和医护。在张悦然的印象里,祖父独善其身,专心医学,对政治、做官都兴趣不大。
起初,张悦然不太知道怎么把故事讲完整。直到2011年,多年以后她再次回到父母居住的山东大学家属院。
家属院相对封闭,她记得,老师从前经常告诫,“不要跟社会上的孩子玩”。院里新盖了很多高楼,但“变化非常慢,不像城市的其他部分”。往日的树木、平房、垃圾站,甚至看水果摊的女孩和卖报的男人都还在。她突然意识到,那些是自己的童年痕迹。
童年并非一直如此珍贵。不到20岁,张悦然就迫不及待离开了济南——“一个面目模糊的北方城市”。接近30岁时,她想真实地书写故乡。小说的背景,就设在济南。
“躲进你爸爸的时代”
张悦然决定这样讲述故事:先返回自己的童年,再返回父辈的童年:父辈童年经历“文革”,人生受到影响,继而又影响了下一代。
199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对面,以三株口服液闻名全国的三株集团成立,一天天“日新月异,像一个大帝国”。一些老师无所适从,怀疑起学问的价值。张悦然记得,有些老师瞬间成了商人、餐厅老板,有些人公派出国,再也没回来。张悦然的父亲,则一直留在学校。
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一部分来自张悦然自己的父亲。小时候的张悦然,经常兴致勃勃地画画、剪纸,父亲总是表示不屑,让她顿时觉得“一盆冷水浇下来”。
“那时我对一切充满希望,特别有热情,但身边有个很幻灭的人,对我童年的触动非常大。”张悦然认为,这样的经历使80后缺乏爱的能力,“不会表达感情,或觉得得到的爱不够多”。
刚写小说不久,张悦然就创作过女孩弑父的故事。女孩父亲是画家,长期让她一动不动做模特,态度粗暴。男孩想邀请女孩参加舞会,但直言她的嘴唇太苍白。女孩没口红,想找父亲的红颜料代替,发现父亲根本没有红颜料。她最后杀死父亲,用他的血涂红嘴唇,出门参加舞会。
张悦然经常写到弑父。弑父之外,还有炽烈的恋父。“她们爱的这个父亲,其实不是真实的父亲,而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像一个蜡人的存在。”张悦然形容道。
《茧》里,李佳栖的教授父亲和张悦然的父亲不同,最终离开校园和家庭,去了北京,成为往返于中国和东欧的国际“倒爷”。“倒爷”存在于特定年代。他们一夜暴富,用大麻袋装卢布,航空运输兴起后迅速没落。
“倒爷”的故事,是张悦然跟一位表姑聊出来的。表姑当年去俄罗斯做生意,还记得火车上有很多狗在跑。1990年代,人们喜欢的贵宾犬、贵妇犬,许多是从莫斯科运到北京的。
小说《茧》中,施害者、李佳栖的祖父一直逃避罪责。李佳栖则执著于探寻往事。男友指责她:“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
很多朋友告诉张悦然,自己认同李佳栖的男朋友。他显得更正常,而李佳栖有点“作”。
张悦然更认同李佳栖,“做一些无用功,但清晰地去走一遍父亲的路,了解他们的历史。”
《茧》首发在文学杂志《收获》2016年第二期。有人觉得,她应该用更大篇幅去写李佳栖男友那类人——无视历史,轻巧活在当下:“他们才是真实存在的80后主体。”
但也有90后读者给张悦然微博留言:不会忘记过去发生的事。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