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腐|为什么说境外追逃难,追赃更难?
 2016-01-05 16:13
2016-01-05 16:13
文|黄风(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 )
相对于非法集资、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的外逃情形而言,腐败犯罪案件的外逃情形具有某些特别之处,在境外追逃追赃中往往遇到一些特殊困难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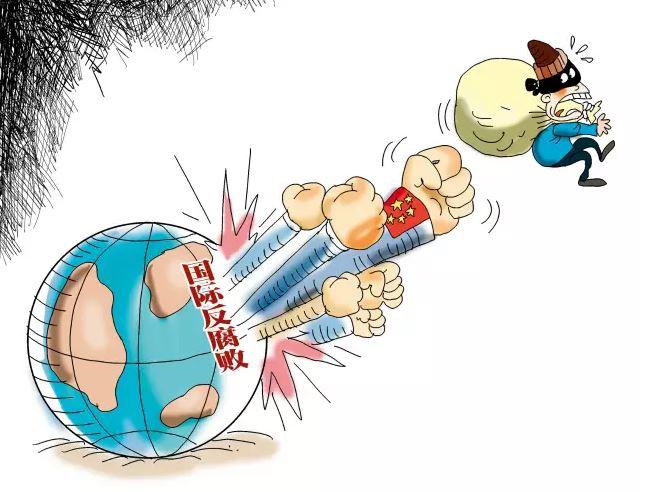
境外追逃难的外部因素和自身不足
大量腐败犯罪的案例表明:逃匿境外,并不一定是贪官为逃避打击而选择的退路或者下策,而常常是贪官腐败进程的环节之一,是腐败活动所欲实现的一项目标和上策。
为了能够在国外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腐败案件外逃人员通常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作为首选地,想方设法为自己和家人获得合法居留身份。与此同时,他们采用各种洗钱手段向境外非法转移资产,或者将腐败交易的付款地选择在自己的逃匿目的地。
由于腐败案件外逃人员往往在逃匿地已获得移民身份,受到当地法律的保护,凭借非法资产,可以到处购置隐秘房产,随时变换躲藏地点;即使陷入不利,也可聘请当地最有名的律师为自己辩护,穷尽所有法律程序和救济手段予以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像针对非法移民那样针对这些手持“绿卡”者实行非法移民遣返。

腐败犯罪外逃人员还会使用另一个撒手锏对抗引渡或遣返:利用原有的公职身份,把自己打扮成受到或者可能受到“政治迫害”的公共人物,申请政治避难,博取庇护或同情。
虽然我国已经与39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但是与发达国家缔结的引渡条约数量仍然较少,尤其是对于美国、荷兰等在引渡问题上持“条约前置主义”态度的国家,引渡合作的可能性目前基本不存在,从而使得像杨秀珠这样的逃犯有空可钻。
对现有国际条约资源利用率低,也是我国对外开展刑事司法合作的不足之处。在境外追逃中,我国主管机关比较习惯于通过警务合作查找、缉捕和遣返逃犯,不大善于运用双边引渡条约或多边公约引渡条款打好法律仗。例如,近年来,法国向我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有4件,我国向法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只有1件,而在法国司法部逃犯数据库中,受到通缉的中国逃犯则有一百余人。
从工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主要依靠中央主管部门处理国际刑事合作案件,省以下刑事司法机关尚未充分发挥境外追逃办案主体的作用。对国际刑事合作的规则和被请求国法律制度缺乏足够了解和研究,一些司法合作请求材料不合国际规范,或存在明显漏洞,导致相关请求被外国主管机关束之高阁或者在庭审辩论中被驳回。
在开展“劝返”工作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和司法解释,在认定接受劝返者是否属于自动投案或自首问题上各地司法机关做法不一;在“劝返”过程中随意承诺或者事后不遵守承诺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劝返”刑事政策的攻坚力、稳定性和可信度。
从更深的层次看,发达国家向我国引渡或者遣返逃犯的最大顾虑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能否确保被引渡或遣返者的合法诉讼权利,给予其基本的人权保障,并实现公正司法。
境外追赃成果寥寥的主要原因
贪官外逃一般伴随着资产转移。境外追逃方面,目前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在境外追赃方面,工作却明显缺乏力度,成果寥寥。造成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如下:
1.犯罪分子向境外非法转移资产通常采用洗钱的手段。
通过洗钱方式完成的资产转移大大增加了办案机关甄别和向外国证明资产非法来源的难度。
在我国现行刑法和司法实践中,洗钱罪通常仅限定于“协助”上游犯罪人掩盖或者转移犯罪收益的行为,如果贪污受贿者自行通过洗钱活动掩盖或者向外国转移其犯罪收益,此种“自洗钱”行为是不被单独定罪的,只被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这种“自洗钱不入罪”的做法非常不利于对相当大一部分洗钱行为的调查、打击以及相关的国际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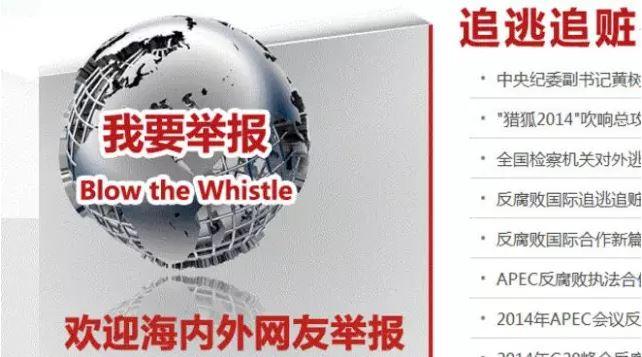
2.财产权受到各国法律以及国际法的特别保护,而现有的国际条约均强调有关国际合作须在资产流入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境外追缴资产还可能牵扯诸如财产的归属、转让、分割、第三人权利保护等复杂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和问题,相关的民事诉讼往往旷日持久、耗神耗资。而我国主管机关则缺乏对外国资产追缴法律制度的研究和了解,一些办案单位在实践中不得要领,畏难情绪严重,甚至一筹莫展。
此外,我国刑法中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体现着陈旧落后的财产刑观念,在国际上被认为背离了没收财产的宗旨,构成对被判刑人“基本人权”的剥夺,此种没收财产刑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摈弃,依据上述没收裁决提出的资产追缴请求一般会被外国所拒绝。
3.各国都欢迎境外资金的流入并且希望这些资金能够稳定地保留在其境内发挥效益,资金流入国有时候可能因本国经济利益而不那么情愿满足资金流出国提出的追缴和返还请求。
此外,根据外国请求调查、控制、没收、返还财产常常需要资产流入国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的国家因此而态度消极,不愿意为挽回别国经济损失而付出资源代价。而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按照《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没收令的制度,我国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难以依据现行法律执行外国提出的冻结和扣押资产的请求。由于我国与外国开展的资产追缴合作缺乏“互惠”基础并且基本上无国内法可循,使得一些国家更加不愿意执行我国提出的关于冻结和没收犯罪资产的合作请求。
多管齐下,编织追逃天网
基于对上述困难和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反腐败境外追逃工作应当着力开拓与发达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关系,努力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所确定的基本方针:“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 ”
对于外逃的腐败分子,在追逃时同样应坚持引渡、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劝返多管齐下的方针。对于那些已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外逃人员,应注重查找其采用作假、欺诈手段获取移民身份以及通过洗钱手段向当地转移资产的证据,使得当地主管机关能够对其采取法律行动,取消其合法居留身份,追缴其非法资产,创造遣返或引渡条件。

外逃贪官虽然具有较强的抗拒“劝返”能力,但在特定情况下也有心理极度脆弱的一面。我们的“劝返”应当注重心理战,在他们落魄和绝望时指明出路,以行动确保引渡或遣返的实现。
拓展与发达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关系,需要树立和维护我国依法治国的法治形象,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充分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切实遵守公正司法的各项准则和证据规则,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并在立法上“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同时,我国应当尽快出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为广泛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提供必要和有效的法律依据,担当起一个大国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腐败犯罪中的国际合作责任,努力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追逃追赃合作朝着互惠、双赢的方向稳健发展。
加快改革步伐,助力境外追赃
境外追缴犯罪资产是政策性和专业性极强并且涉及面极广的工作,针对种种问题和困难,笔者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我国的反洗钱立法和监管,改变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上游犯罪行为人“自洗钱不入罪”的做法,加大对“自洗钱”行为的调查和打击力度。在反洗钱监管方面,应当尽快创造条件将房地产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拍卖行等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到反洗钱义务人的行列。
二、转变“重惩罚、轻追缴”和“重追逃、轻追赃”的倾向,尽快改革我国现行的财产刑制度,将没收财产的范围严格与违法所得的数额挂钩;在立法改革完成前,尽量在审判中用罚金刑取代“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三、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业通过在境外的民事诉讼追回资产,建立基金会,为遭受经济犯罪侵害的财产受害人通过境外民事诉讼追回资产提供必要的援助。
四、在国际追赃合作中,应本着最大限度降低国有资产损失的原则,积极采用和接受“分享被没收资产”的做法,以提高资产流入国的积极性。尽快通过制定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引进相互承认和执行罚没裁决的制度,为追缴腐败资产的国际合作奠定互惠互利的坚实基础,并使之常态化和法制化。
【来源】南方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