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可杀,不可秃,头发为什么很重要?
当90后都要进入“谢顶大军”时,这些张扬的年轻人们似乎预见到了自身健康的转折。
头发,是衡量身体健康的明显指标之一,如果开始脱落的话,面对着与自己在工作生活上平行的女性,她们还是乌黑的发际线,哪个男人不会感到自行惭秽呢?
“知道”(微信号:nz_zhidao)告诉你,头发为什么那么重要?

秃不秃头很重要?嗯,可能是的。
马踏青苗的曹操不能自戕,但为了申明军纪,只得割发代首。这说明曹操并非是一个油腻腻的中年秃子,有头发,并且还要“白发三千丈”,这才算是古人的标配。当然,头发的密度和长度那都属自然生长,谁都不相信古代人到中年不会没有秃子,只不过头发的“长”和“多”的问题罢了。
美国毛发研究者库尔特·斯坦恩(Kurt Stenn)曾说:“没有头发的人少了一件在人际交流中很重要的工具,一种非语言并且能远距离起作用的装置。”他还提到,“我们通过留长发、剪短发、烫卷发、拉直发、染颜色甚至完全剃掉等方式精心编织要传达的信息。”
头发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重要?它从古到今传递了什么信息?
谁不爱头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里的这段话,给头发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在古人看来,“发为根也”(许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对发有“肾之体在发,血之荣以发”的解释。头发不仅仅是身体的一部分,更是某种精神和文化的指代,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政治价值。
就像那一夜白了头的伍子胥,一个心理憔悴和焦烦的中年人,黑转白的时间之短让人咋舌。当然,我们都晓得这里面有夸张的成分,但这份文化和人类社会里的夸张演绎,正好把头发“盘”在了政治的桂冠上。当头发成为社会象征的时候,它也完成了由生理到精神层次的蜕变升华。在世人眼中,那苍白的标签,是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时间幻灭,也是生命和死亡、激情和沉沦、复仇和宽宥的暗喻。伍子胥顶着一头白发成功出逃,但篡位成功之后的王莽,却不想让自己的臣下看到自己一头的白发苍苍。登基之前,他要“欲外视自安,乃染其须发”。
王莽是不是第一个染发的皇帝不得而知,但白转黑的非自然人为做法,证明了世人对头发的重视程度。他用头发证明自己的健康,进而延伸出自己对政局稳固的掌控。这事实上并非开化的文明人的专利,因为即使在动物界,也有通过毛发或牙口等身体器官,来证明其的健康或者强壮的现象。不同的是,动物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大自然主导的行为,大自然驾驭着它们的选择方式。人贵为万物之灵,可以通过自我干预的方式,来随意处置、变更、利用、展示自己的头发。
与王莽的染发不同,道家的头发,永远是白发如雪染,或许跟他们提倡的道法自然有关吧。在道家看来,天地万事万物都由“道”来主导,人的各项生理指标,也都由道来从中维持。于是,从青丝到银发,那就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当头发全白,就是这个过程到达极致的时候。但从另一方面看,讲求自然主导一切的道人们,又在追求长生,这似乎又跟自己的主导理念相悖,那一头飘逸的白发,又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社会意义标签——至少在世俗人的观念里,只听说过白胡子老道和白头发的神仙,没听过有黑胡子和黑头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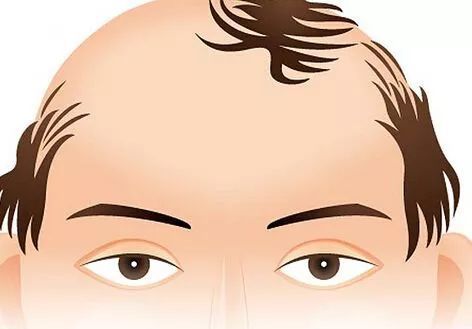
士可杀,不可辱头发
从蓬头小儿的垂发,再到弱冠之年的束发为冠,有强烈入世情结的儒家把头发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士大夫还是白丁,虽然有着社会等级的差别,但顶上之发却别无二致。人们盘头洗头,但却鲜有剪头。一来是头发毁伤是对父母的大不敬,是一种文化情愫限制;二来在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看来,头发代表了一个人的心。于是乎,无论男女在古代一旦披头散发出现在公开的场合,那即意味着这个人的生命似乎要走到尽头了。
屈原沉江之前,应该是梳理过自己头发的;上刑场的文天祥,在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抉择面前,也是一幅披散头发的尊容。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凄惨景致,那风吹起来的“絮”,又如汉族士人散状的头发,失了桂冠,也就失去了本民族倡导的根本。等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站在法场上时,他的凄然一笑和大义凛然,却只能配以摸着自己的光头,这场面想象起来有些滑稽。毕竟,在满清两百多年的辫发统治下,似乎已经让汉人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到究是什么了。
明亡的时候,很多士大夫宁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自己的头发;清亡的时候,不少的遗老遗少又坚决要拖着那根“长尾巴”。在头发形状的变更面前,往往承载着文化和政治更迭的双重含义。虽然现代的很多人,对清人的头发以及头发背后拥含的意义有很大保留,但事实上,无论是明亡的“留发不留头”还是清亡的“留辫”,那仅仅只能称为一种表象。尤其对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的中坚阶层而言,头发是什么样的形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批人心中的形式。就如辜鸿铭所言的意义,头顶着辫子不可怕,脑子里留着辫子才可怕。
表达承载的理念
但头发的文化,又是一种极其明显和简洁的宣示。它往往一目了然,就跟世人穿何种衣服一样,透过不同的表层叙述,把承载的理念表达出来。和男性变换发型不同的是,女人似乎跳出了这个框框,虽然清代的男人们都留着光头拖着辫子,可紫禁城里的慈禧,还是和同时代的民间女子甚至前朝的女人们一样,对保养自己的长发很看重。可是在男权这一面,女性对自己的头发却并不具备发言权。
“云髻峨峨,修眉联娟”。(曹植《洛神赋》)对女性头发的赞美,往往出自男人之口。无论是“鬓似乌云发委地”还是“鬓挽青云欺靛染”,在长度和色泽上,男人对女人头发的审美,是极其严苛的。在男人眼中,女性头发更长和更黑一点,永远都不为过。甚至于在至高无上的仙界,男神永远都是一头白发,而女神则从层次低到高,都是一团乌黑。
就如西门庆和潘金莲偷情一样,“金釵倒溜,枕头边堆一朵乌云”。乌黑的头发不单单是一种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在生理上也预示这是一个妙龄女子而非白发老妪,在一定程度上能更猛烈的激起男人的情欲。如果说男人的头发是一种政治宣告,那女人的头发就代表着情欲上的暗示。当然,这份暗示是男人赋予女人的,而且这暗示只对异性有效,换言之女性恬然接受自己的长发标签,并且不认为这是男性对自己的强加灌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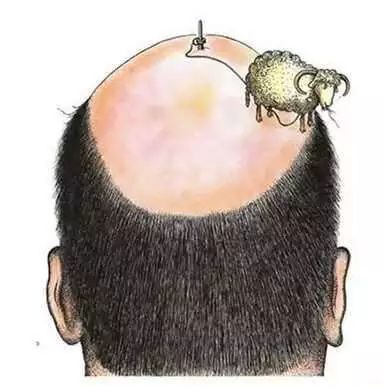
不一样的“定型摩丝”
如今的时代虽然变了,但头发承载的社会政治价值并没变。对各国上层的男性而言,虽然原始生理上头发的颜色和形状不同,但在寻求最大公约的基础上,大家都心照不宣。从头发的形状再到色泽,各国的领导人选择标准无非都是以展示健康、大众接受程度、代表自身形象等方面为基础审美的。
同时,现代社会的公共人物几乎无时不刻不在镁光灯面前,如果不能通过头发展示出自身的良好形象来,那无形中会传导给社会很多未知因素。因此现代社会的多数公共人物,一旦头发的形状和色泽在公开场合里展示过,那么其后在他/她自己漫长的时间岁月里,也就基本固定不变了。
而且,借助于现代发达的科技,可以人为的让头发长时间保留成一种形状和色泽。于是在现代社会的文化政治寓意里,头发不单单展示着健康,还代表着这个人身处阶层的稳固和安全。看看国内那些落马的大老虎们,事发的前与后,头发的变化落差很大。即使是奥巴马,在任期间和卸任之后的头发颜色,也发生了改变。
而对现代女性而言,消费心理、情欲观、审美等各方面的不同,女人的头发如万花筒一样多姿多彩。人们越来越想追求个性,然而在资本主导的时尚和流行元素面前,真正个性的头发到底是什么样子,反倒是辨别不清了。
反过来再看男性,虽然90后的“恐秃症”仅仅是一种调侃,背后的文化寓意,似乎是男性对社会主导权受到女性冲击,越来越感到不稳固的恐惧。在倡导男女平等、平行的今天,女性权利虽然还不至于全面铺开却一直在稳固增长,某些方面已经在事实上对传统的男权构成了包围。当90后都要进入“谢顶大军”的时候,这些张扬的年轻人们似乎预见到了自身健康的转折。头发,衡量身体健康的一项最明显的指标,如果开始脱落的话,面对着和自己在工作生活上平行的女性,看着她们还是乌黑的发际线,哪个男人不会感到自行惭秽呢?
更何况,女性头发的高男人一头,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表现,大部分是人为审美下的产出结果。所以,90后要变秃,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男性一种提示,在自身形象的维护上,男人也应该像女人一样,要多投入。
不过话说回来,头发无论怎么样,只要不是病理性的变化,还是自身的最好,美丽的形象固然很重要,但没有了岁月自然刻画的印记,也就没有了生命的经历坐标,你说呢?
 快来抢沙发
快来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