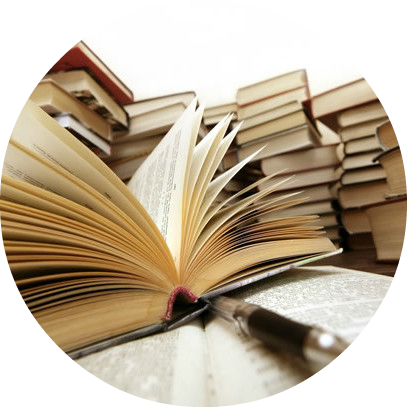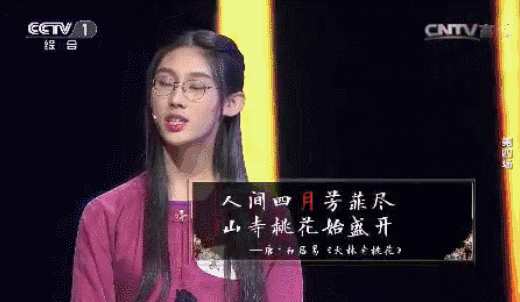《中国诗词大会》火了武亦姝,语文老师却担忧了……
春节红了一位才女,火了一档节目。
“00后”复旦附中女生武亦姝凭借在《中国诗词大会》惊艳的表现,与节目一起刷爆了朋友圈。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赞誉,该校语文教研组长黄荣华却表达了一丝担忧。
文化综艺节目的“圈粉”之路
武亦姝之前,来自《中国成语大会》的“白话灵犀”组合也曾引发刷屏热潮。这对由两个来自河北邯郸学院的小姑娘组成的参赛组合,一个机灵可爱,一个沉稳坚定,比起“颜值”更让众网友佩服的是她们大气的台风和对四字成语信手拈来的熟悉度,这与如今武亦姝的受追捧如出一辙。
“白话灵犀”组合
“大会”比拼的是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但对荧屏前的观众来说,看点不只是选手对诗词的识别和背诵而已。在选手答题之后,由学者嘉宾介绍这首诗词的内涵、诗人的创作背景等才是更让人如痴如醉的文化大餐。正如嘉宾王立群在微博上所说:“背诵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理解。”“果真生活不止前方的苟且,还应该有诗和远方”,有网友感慨,“看了几集《中国诗词大会》,收获很多,最喜欢的就是蒙曼、郦波、王立群等老师对诗词的解读,每一句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中国人的诗心一直在,但需要被激活。”诚如《中国诗词大会》另一位嘉宾、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所说,“大会”系列的走红其实暗合了社会中本就埋藏着的了解传统文化的需求,同时又能改变以往文化宣传“自说自话”、“高高在上”的说教口吻,将娱乐节目模式和文化传播结合起来,观众的距离感消失了,传播效果自然好了。所谓荧屏清流,“清”指其品质与品位,“流”就是要真正流到观众心间。
当然,“大会”系列并非尽善尽美,它们的走红恰恰是观众对于文化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要将跨越时空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聚焦传统文化的综艺节目不能止步于“赏”、“品”、“寻”的境界。而在诗词、谜语、成语等传统文化内容全被挖掘一遍后,文化综艺节目又该如何再辟蹊径?
武亦姝因古诗文走红,语文老师却担忧古诗文教育
“这个00后美少女满足了人们对古代才女的所有幻想。”网友点赞了一位00后女生武亦姝,她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复旦附中”)。
16岁的武亦姝在2月1日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电视节目中,凭借丰富的诗歌储备量赢得比赛。在后来的网络传播中,她典雅从容的现场表现,收获大量关注和赞叹。
她的一名同学称,武亦姝在该节目中背诵的带“月”字诗句,大多出自该校校本教材《中华古诗文阅读》。面对赞誉,这套校本教材的主编之一、复旦附中语文教研组长黄荣华却表达了对当下古诗文教育的担忧。
他表示,武亦姝只是个例,更多的与她个人爱好和积累有关。她的走红,反衬出古诗文教育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家长质疑为什么要背那么多古诗文
《中华古诗文阅读》第一册就选了《诗经·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一在电视节目中为武亦姝赢得最多赞叹的诗句,正出自这首诗。
这套校本教材一共六册,在复旦附中和语文课本同为必修,融入日常教学,其教学内容大大超出考纲要求。
黄荣华说,一个学生两年里找了他五六次,问为什么要背那么多古诗文,可不可以不背。也有家长质疑:为什么高考只占6分的古诗文默写,在复旦附中平常的测试中要占到二三十分,要学生花那么多时间的时间去背?
在接受采访时,他再三表达了对当下古诗文教育情况的担忧,很多中小学语文老师正在做的是“考什么就教什么”,“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高的产出、最高的分数”,让语文教学落入“工具理性”的陷阱。
反映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学生往往直接记下结论,“再放到某个地方去得分。”黄荣华拿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举例说,“如果失去了去追究为什么是沉郁顿挫,不去追问为什么是杜甫这样一个诗人,成为唐代站在诗歌顶峰上面的人,他对中国文化前代有什么接受史,对后代有怎样的影响史,我在他身上获得了什么?其实这个就不是基础教育,就是技术教育。”
在他看来,坚持“高标准”古诗文教育的压力,近年来似乎越来越大,考试分数稍有走低,反对声便又高过一浪。好在古诗文教育得到了校方的支持,这所沪上知名高中,一直以坚持素质教育著称。高一第一次家长会上,他就告诉家长,既然选择了复旦附中,就要接受这样一种教育,“他们也觉得有道理”。
希望传统文化成为学生成长土壤
黄荣华相信,这样的古诗文教育可以让学生在高三时轻松应付考试,还能向学生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版图,他要让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学生成长的土壤。
凭借丰富的诗歌储备量、典雅从容的现场表现,武亦姝在2月1日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中大放光彩,她不仅赢得了比赛,还在后来的网络传播中收获大量关注和赞叹。
在接受采访时,黄荣华强调,武亦姝只是个例,“谁编《诗经》不会把《七月》编进去?但我可以说,这届学生学完这本书(指《中华古诗文阅读》),能背出来的可能就她一个。”
这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还认为,武亦姝的走红,反衬了古诗文教育的现状,“因为普遍对古诗文缺乏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出现了这种追捧。”
这一稍显悲观的看法,或许来自于他的高追求。他希望达到的是,让学生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他的精神,根植到底部,作为一种底层展开。”
多位复旦附中毕业生的说法印证了黄荣华的想法。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学生李静智说,虽然背诵的许多内容已经忘记,但在诵读经典时,心灵受到的触动、激发的思考和从中吸取的养分,将让她受益终身,“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学会了做一个有人文精神的‘人’。”
她还说,班里大部分学生都能按照要求背诵所有篇目,“大家捧着《论语》相互考考,也构成了我们共同的回忆,特别美好。”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施佳蔚也表示,母校的古诗文教育让她觉得既幸运又值得,“比如《诗经》,课本里最多选取其中的一两首,如果没有学校和老师的硬性要求,我们可能就不会想到去接触这些内容。”
小伙伴你怎么看?
欢迎在文末留言!
本文综合自上观新闻、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