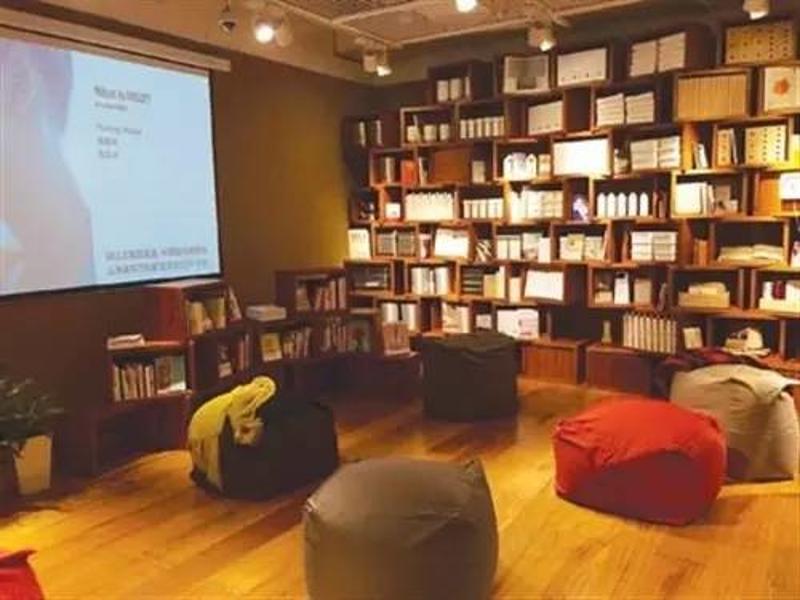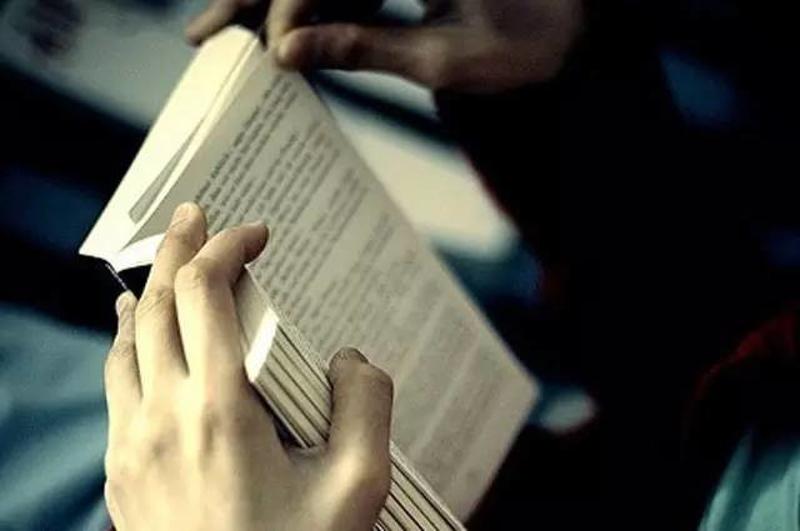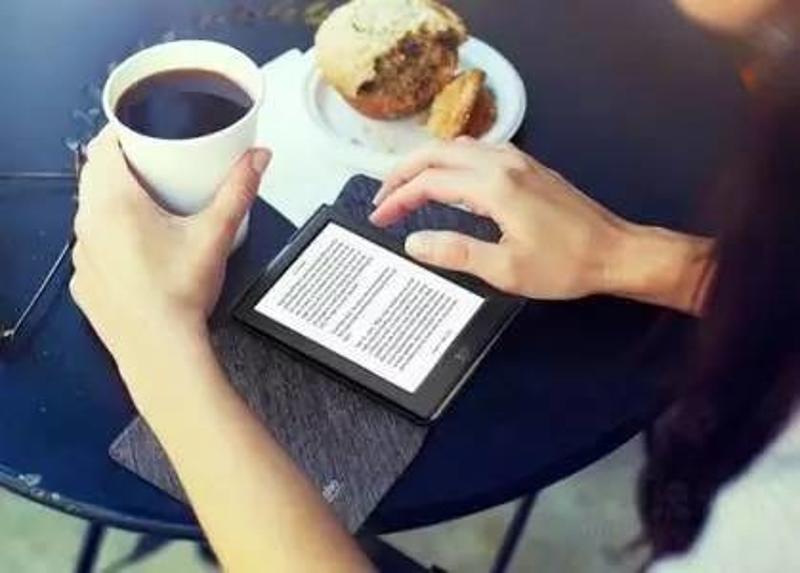【夜读】人为什么要阅读?提升、唤醒自己,还是社交需要?
作者:林景新
那天我在学院主持一个读书会,这是一个MBA、EMBA、总裁班学生组成的一个读书俱乐部,一个月举办一次。
这些工作繁忙、事业蓬蓬勃勃的企业人士,一谈起读书个个都活跃积极,兴致勃勃,仿似读书比做事业更带来充分的心灵满足感。作为一名教师,我开始甚是感动,如果一群最没有时间读书的人都愿意付出大量时候来阅读、求知欲望如此强烈,这个时代必定飘满了知性的味道。后来在读书会上,一名我所教授的EMBA班中穿着最珠光宝气、最不认真学习的一位女士,站在众人面前悠悠地说:阅读是一种最高贵的行为。言毕,众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无数男士向她投以赏赞的目光。
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在这个时代读书不一定为求知,许多时候读书已蜕变为社交的需要。
我参加过一些高大上的聚会。餐毕,绅士淑女们谈到读书的论调就是分享阅读的重要性:你可以出身贫微,你可以孤身无人爱,你可以过得苟且偷生,但是你只要阅读,你就高贵;你只要阅读,你就气质超然;只要你阅读,你就书中自有颜如玉。在当下这个知识的时代,任何聚会中最容易找到的共鸣话题之一就是谈读书,每一个谈自己多爱读书的话题总能引来一片赞赏之声。
我越来越有困惑之感:阅读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是一种求知的需要?是一种进步的需要?抑或只是一种搭讪需要?
阅读的重要性是为自己建立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但是唯阅读至上论或阅读高贵论却会把我们获取知识的渠道狭窄化——人的知识既来自阅读等书本的教导,更来自自然模仿、社会学习等外部知识吸收。远古时代,人强大的自适应力就决定了一个人就算没有进过学校,不阅读什么书籍,他在恶劣的环境里,他通过观察、通过总结、通过提炼、通过思考、通过反思、依旧能摸索出他应该所掌握的东西。
每个人有很多潜能等待被唤醒。人不断向前进化的基因决定了人从一生下来就会自我调动所有感官去获取进步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阅读是掌握知识的一种途径,但它并不是全部,更不是唯一。一个把读书经常挂在嘴边的人,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以阅读为职业的人,比如说图书编辑;第二种是屌丝,始终想在书本中找到摆脱屌丝命运的一种可能,现实屡屡碰壁,所以他不断需要去书中寻找可能的答案;第三种是把读书视为一种炫耀或社交的话题,比如某些社交达人。
在高校任教多年,我认识了很多皓首穷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阅读量非常惊人,文、史、哲、天文几乎无所不读,无所不通。但是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聚首时,很少提及读书的乐趣或读书的心得。阅读对他们来说,那只是跟吃饭、喝水、睡觉一样,只是没啥值得专门一提的平常事。因为对他们而言,读书与生活,本为一体。
阅读是一种求知的方式,但把阅读视为高贵行为却是一种无知——读书很有必要,但不一定就高贵。在书出现之前,人类已经进化了很多年,人的自适应力超乎了一切书本的指导。如果你把读书视为进步或获得文明的唯一阶梯,你就削弱了人自身强大的自适应力,比如从观察中获得知识、从交流中获得经验、从自然中获得技巧、从动物中获得模仿、从静思中获得总结。那些常常从社会、人群、自然、工作实践获取灵感的人,往往比唯读书为高贵论的人,更具强大的自适应力与生命传承力。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很多时候却成为人逃避社会压力、屏蔽自我适应力或者掩饰无知的最佳借口。
作为灵长类动物,人不过自然一分子。行为不过是生命的本能驱使,高贵与否不过是人为赋予的自我满足。日日阅读的名士不一定就比引车卖浆之徒更有生活的智慧、言必称爱读书的人不见得就比街头浪者道德高尚。
当你站在不维度看待阅读时,对阅读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去看待其他生物,你会觉得一览众山小;你以一个蚂蚁的视角去看待一切,一切就会变得很高大。所以,一个人从不同社会阶层去看待阅读,心态自然不一样。李嘉诚需要阅读吗?肯定是需要的,但是我相信他的阅读和一般人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有些人视阅读为改变命运的行为、有些人视阅读为高贵的行为,有些人却只把阅读视为一种唤醒,启迪自我智慧的唤醒行为——苏格拉底认为人生而有知,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学习,更要学会唤醒。
苏格拉底想表达的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人都有自适应性,我们要学会内寻找力量而不能纯粹向外寻找力量;惟读书高贵论只会削弱我们自身向内寻找力量的可能。第二:人必须要求知,但阅读只是求知方式之一。对话、倾听、思考、呆坐甚至做梦都是求知的一种方式;第三:学习是一种唤醒的行为,带着思考去寻找寻找唤醒的感觉,阅读将更有意义。
我一向喜欢阅读,我也一向喜欢那些喜欢阅读的人。但我不喜欢那些动辄把爱好阅读挂在嘴边并把阅读抬到高贵行为的高贵口号——那些口号不过是一种打着求知旗帜其实无知的幌子,一种充满约炮味道的社交装逼行为。
多么希望,在某个阳光晴好的午后,我趴在牛背上悠然入睡。风把书从我手上扯落,那破碎的书本上,印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标题《阅读是门槛最低的装逼行为》。
本文作者 / 林景新博士,高校教师,著有『远方有多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