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唯一一届“信访班”:信访局不招,过半已改行
澎湃新闻 2016-07-04 16:09

2015年年底,贵州大学信访班学生周舟得知“国考”(公务员考试)本专业几乎没有合适职位可报,他有些激动地找院系领导要说法,并把领导跟他私聊的内容发至学院的QQ群里。
次日,同学陈俊经过周舟宿舍门口时,学院教师已结束对周舟的“拜访”。陈俊清晰记得,教师的临别语是:“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话啊。”
周舟留在屋内,一声不响。
半年多后,6月28日,贵州大学2012级信访本科班34位学生毕业,这是该校首届信访班,目前来看也是最后一届。
此时,学生们到手的学位证上写着法学学士、社会工作专业——早在5月,辅导员就要求他们求职填资料时,一律在专业一栏写上“社会工作”。
作为211院校的贵州大学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东南的花溪区,依山傍水,进入六月雨季,黄昏下一场大雨便能冲刷掉白天的灼热。
信访班的一些毕业生仍为毕业的出路焦灼难安:他们中不少人当初拿着“社会学”录取通知书被调剂进“信访班”;入校第二年起,突然发现成了“独苗”,没再见过学弟学妹;而当大四求职时,又被信访局告知要“法学专业”而挡在公务员考试门外。

四年里,先后有三位学生离开原本有37人的信访班,一位在大二那年转去了法学专业,另外两位在大三第一学期相继选择了退学。截至毕业,随机采访的18位信访班学生中,无一人从事信访相关工作。
信访专业该学什么?出路在哪?这些问题从信访班招录之后,就成为学生们共同的困惑,直到毕业,仍是难解的谜团。
报考:“服从调剂”而来的绝大多数
孙伟的家在与重庆一山之隔的黔西北——铜仁市土家族自治县,从家到在省城贵阳的贵州大学要翻山越岭。
2012年,他拿到贵大法学院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时,父亲高兴坏了,在村寨里摆了十几桌宴席,端上野味,为当地大山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喝彩。孙伟说,那天亲戚朋友邻居给的红包累加起来,够他大学四年的学费。
报考政治学专业的孙伟,到校才知道自己被调剂到了信访专业。因为延迟到校,他接收信息的回路相较其他人更长,当女生宿舍都开始互传信访专业包分配工作的消息,他还在犹豫用一百块向学长买床被子是否合适。
一位贵阳当地的媒体人向澎湃新闻透露,贵州大学信访专业系“行政力量推动”,主要考虑当时贵州信访人才稀缺而设。
贵州大学信访班设在社会学专业下,划入法学院。与国内几所也开设了信访方向的高校相比,该校信访班“开张”显得尤为低调,少有公开报道,校方也仅在官网挂出一则专业培养方案宣告其成立。
就连此后教授信访班学生专业课《信访工作沟通与技巧》的李开学也是在一年后,“受托给他们上这个课,才知道贵大有这么一个信访专业。”他在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时说。李开学曾任贵大信访办的正处级干部,现任贵大药学院书记。
与孙伟不同,另一位信访班学生林爽起初目标就很明确,在县城法院工作的姑妈在她高考填报志愿时出主意:国家的信访人才缺口大,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层出不穷,她建议林爽大胆试填这个贵大新开的专业。
遵义姑娘林爽高挑清秀,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起话来条分缕析。她在信访班连任了三年班长。
林爽发现,班中绝大多数同学是在报高考志愿时填了服从调剂,然后才分到信访专业的。拿她的五个室友来说,除了三个法学院的学生,与她同班的范心欣和赵依,一个第一志愿填的是经济学,另一个填的是法学,她俩之前对信访专业都毫不知情。
教育部高教司、综合处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2012年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专业目录中并没有信访专业。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信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翟校义向澎湃新闻解释说,国内的学科规划布局,一般从上到下依次是大类、学科、专业、方向。方向只要向教育部备案,学校有权自主设立。类似信访这种自设专业或者交叉学科,不在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
开学:迷茫中被召集开会“画了一块饼”
开学后,法学院下属的几个专业相继开了以介绍学校培养方案和专业就业为主题的情况介绍会,但信访班迟迟未开这个会。
“(我们班)很多人都是调剂过来的,快一学期的时候就很迷茫,没有归属感。”林爽说。
第一学期临近尾声,信访班邢娜计划要转到法学专业的消息,打破了学生们沉默的困惑。
“大家还没搞明白这是什么船,就有人要下船了,你说心里什么感受?”林爽听邢娜说了计划,“一年以后如果学业特别好,有学院的推荐可以转专业。”
林爽向班主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找到院书记庄勇,书记隔了一段时间后把我们班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议。”
在会上,出身社会工作专业方向的庄勇给信访班学生绘制了一幅美好的图景。
“法学院的书记召集大家谈,说国家缺人才才会有这个专业。知道全国只有我们和沈阳大学有这个专业,我们就觉得好幸福,那时谁都羡慕我们,还传说包分配工作。”范心欣说。
同是信访班的学生陈俊也回忆说,庄勇在会上信心满满,要让信访专业发扬光大,但第二年庄勇调往人文学院当院长。
澎湃新闻多次尝试致电时任法学院书记的庄勇、现任法学院院长的冷传莉求证此事,他们手机和办公室座机均无人接听。
整个大一,信访班唯一的专业课信访学概论由法学院的副教授张林鸿来上,上课主要是阅读教材,要求学生自行复印教材,内容是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的《信访学概论》。

在学生孙伟的这本教材上,有不少上课时走神留下的痕迹。他在书的扉页上分三行写了“国企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然后密密麻麻抄写了琐碎的歌词,竖着连写了两遍“你不要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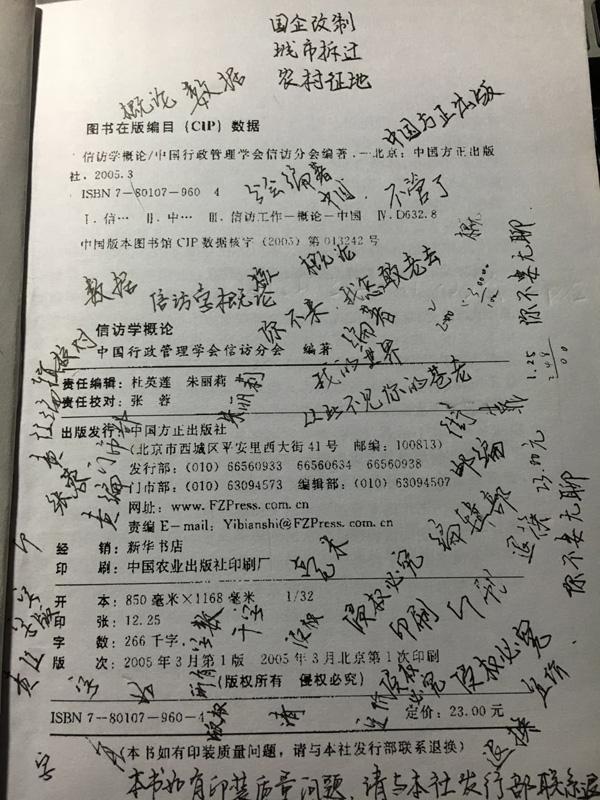
一些走进课堂的法学教师对这个专业的设立表达了诧异,他们认为,将来是法治社会,信访制度会慢慢消失。
“我觉得信访的成本比较低,走司法程序可能要耗费司法成本、法律资源,法学院的老师肯定不希望人们走信访这条路,不然他们培养的律师法官哪还有饭吃?”范心欣想。
停招:信访在学院聊天群里成了敏感词
到2013年暑假前夕,一则消息让贵大信访班的学生再度陷入颓唐,学校的贴吧里流传信访专业将停招。
当年情形,2012年6月起执掌贵大的校长郑强显然最有发言权。
郑强起初表示“有什么关于学校的采访找我嘛”,但2016年6月13日,在澎湃新闻询问信访班为何停招后,郑强的秘书称,校长拒绝任何有关内容的采访。
2013年暑假过后,信访班学生果然没有等到学弟学妹的出现,却又获知,信访班将随整个社会学系,从法学院迁移至2013年8月新成立的公共管理学院。
“我们瞬间变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学生陈俊形容当时信访班的“集体失落”状态。
大一时,学生还会积极地在学院的聊天群里改自己的备注名,比如姓名后加上信访121,表示信访专业2012级1班,但不止一个学生向澎湃新闻表示:“信访是敏感词,无法完成修改,只能用社会学123代替。”转去公管学院之后,原先社会学的前两个班级改称政治学1班、社会工作1班,但代指信访专业的社会学3班岿然不动。
转院不像名称更迭那样简单,而是风波余震不断。
“我们属于公共管理学院之后,又需要法学院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两个学院的联系也不怎么好,导致我们培养计划里的法学课程上不了,比如《侵权责任法》。”林爽说。
“最荒唐的就是,选课系统自动把我们的法学课程换成了社会学课程,还让一个外教来给我们上闻所未闻的《质性研究方法》(注:即定性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范心欣说,光公开的培养方案就改了几次。
“大一大二把法学的基础打好了,让你往上爬,但你爬着爬着发现前面就没有路了。你可以向左转向右转,比如有社工啊、政治学啊……但你知道这不是你想走的。”林爽略显无奈。
关于信访本科班停招,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翟校义曾在2015年接受《 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由于信访涉及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公共管理专业知识,在本科阶段设置该专业方向并不合适。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从2016年开始培养国内第一个“信访博士”;而北京城市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在硕士阶段开设了信访方向。
上课:专业课共四门,三门没有教材
按照贵州大学信访班大学四年的培养方案,信访专业课只有四门,除了《信访学概论》,还有《信访工作沟通与技巧》、《信访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信访社会工作实务》,分别由当时在贵大信访办任职的李开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罗俊松、贵大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陈雁讲授。后三门课没有教材,以教师上课的PPT和印发的讲义为主。
教授信访沟通技巧课的李开学说,自己似乎是被“赶鸭子上架”的。
“公管学院的教学科研科给我打电话说,实在找不到老师上课了。”现任贵大药学院书记的李开学曾在贵大信访办工作过三年,按他的话,是“勉强应承”了给当时大二的信访班上课。
不过,他对这届学生的印象很好:“有些学生还自己积极找专业相关的书来看,很上进。”
在学生林爽的记忆里,李开学所讲述的信访工作是一个解压阀、一个灭火器,注定面对的是“难缠”的人物。
“他说,好多群众就是找一个有人听他说话的地方,找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信访班学生赵依记得,李开学常以自己在学校信访办接待退休老员工上访的经历举例。
但范心欣认为这些只是皮毛:“就教些社交的沟通技巧,比如来一个访民,你要端茶送水。但学校的退休教职工,跟去政府上访的人和诉求大都不一样。”
李开学对此表示:“学校里教的总是挂一漏万,15%在校园里学,85%得到社会上去摸索。”
贵州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副教授陈雁,受公管学院之托教学生信访社会工作实务,她本人主攻心理学,主张以社会工作的方法介入信访。
范心欣觉得这很奏效:“你要知道访民的一些内外诉求,知道他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什么。”
但赵依却在实际运用上碰了壁。她曾模仿社会工作的方法,建议家乡县城的信访局将有类似问题的人分组,分别专项解决。
工作人员却告诉她这想法太天真,“让几个人待在一起,危险系数会增加,他们会在交流过程中,情绪越来越高,越来越激烈。很容易走极端。”
她也发现,让访民聚拢简单、打散就没那么容易,他们习惯在集体中寻求安全感。“如果要让一群人推选代表说明情况,男男女女都会往后退。”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