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访谈:原来,英国人不了解鸦片战争
 记者 宋宇
2016-04-20 22:57
记者 宋宇
2016-04-20 22:57

创造“鸦片战争”这个名字的,是一个英国记者,目的是讽刺英国政府的不道德行为。
在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看来,英国人也对鸦片战争怀有深深的内疚,内疚有时让人道歉,有时让人自辩,英国人选择了后者。
“对英国人来讲,这是国耻,是我们最不应做的事。”撰写《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常因这场战争而愧疚,同时又努力保持冷静。2016年3、4月间,在《鸦片战争》中文版推出半年多后,蓝诗玲来到中国,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华。
中国历史学家茅海建在2007年曾邀请蓝诗玲到北京大学做了三四个月访问学者。她与很多中国近代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一边阅读茅海建的名作《天朝的崩溃》,一边去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
《天朝的崩溃》中的几处细节,令蓝诗玲印象深刻。书中写到的三元里抗英,使她发觉,清朝并不是统一的整体。这本书总结道,奋起反抗的民众意在保卫家园,“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在另一个故事中,伯麦、义律等英国将领遭遇台风,流落小岛,花了一大笔钱请村民送他们回澳门。村民们并不关心战争,倘使他们把这些外貌特征明显的“番鬼”送交官府,鸦片战争可能结局大变。
回国后,蓝诗玲开始搜集英文资料。经过两三年撰写,《鸦片战争》于2011年1月定稿,当年夏天出版。很多英国读者反馈,自己原来不了解鸦片战争。蓝诗玲发现,英国人更关心大英帝国在印度、中东、非洲的行为,他们的遗忘与中国人的牢记对比鲜明。因鸦片战争,西方产生“黄祸论”,中国人则开始反省自身的“民族病”——鸦片战争从清政府眼中不起眼的“边衅”,逐渐转变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悲惨开端”。
蓝诗玲起初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其间,因为短暂学习自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的中国历史,她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产生兴趣,决定转系。
大学三年级,蓝诗玲如愿转去中文系。从那时算起,她对中国的兴趣已经超过20年。她的普通话发音标准,用词不确定,随时查问订正。谈起中国,她口中不时蹦出“国内”这个词,似乎在用中国人的方式思考。1997年,蓝诗玲第一次来中国,到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学习一年。那时她刚从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历史、中文各读两年。
在中美中心,蓝诗玲遇见了历史学家高华。高华跟蓝诗玲谈中国在1949年前后的变化,1980年代的“文化热”等话题,是第一个向她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中国老师。蓝诗玲用中文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高华担任导师,为她介绍了很多一手、二手资料,以及研究途径。回英国读研究生,蓝诗玲选择的题目相近,但研究范围扩大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经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蓝诗玲赴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仍定居于剑桥。蓝诗玲觉得守着剑桥大学图书馆很幸福。这家图书馆是英国的“版本图书馆”之一,英国出版每种新书,都送去备份。那里中文书很多,可以登录中国的论文期刊数据库。研究有需要,她还可以提出购书申请。
蓝诗玲已经做了十五六年的翻译工作,英译过韩少功、朱文、张爱玲、阎连科、鲁迅等中国作家的小说。英国读者看翻译作品比较少,但她发现,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书,数量慢慢在增加。蓝诗玲去年开始研究中国作家张承志。她觉得张承志是个独特的人物:认同“文革”时期的信仰和理想,有伊斯兰教背景,在1980年代出名,写小说强调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三种因素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人,非常有意思,我主要想了解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蓝诗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研究鸦片战争研究对蓝诗玲影响深远。“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先入之见。”她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1 必须用鸦片挣钱,战争就必须打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在蓝诗玲的书中多次出现。蓝诗玲看过中国电影《鸦片战争》和《林则徐》,觉得有助于了解义律这个“黑暗”的角色。在片中,“义律是个淫荡的恶棍,妄图用鸦片奴役中国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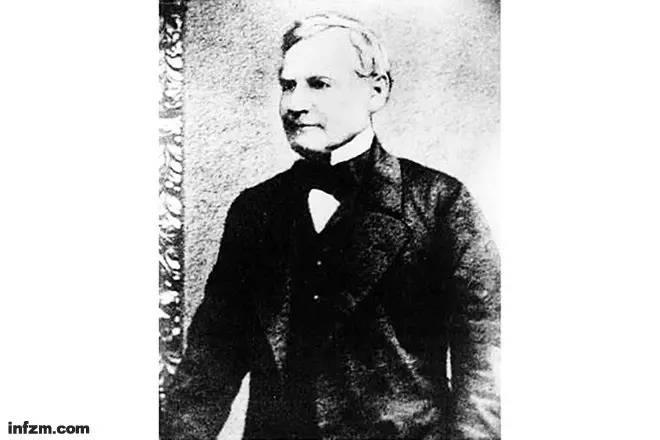
当时,义律在英国国内其实并不受欢迎。《泰晤士报》的评论曾诅咒:“义律的脑袋、身躯和四肢也应该被分割为一千个圆柱体,以警告他所有的家人。”蓝诗玲写道,战后几年,义律的对手琦善都认为他真被砍了头,哀叹:“命真苦啊,可怜的义律。他是个好人。”
义律是废奴主义者,也反感鸦片贸易及鸦片商,蓝诗玲写到了他的复杂:“既有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也惯于投机取巧;既有责任心,又于心不安;既伪善,又自欺。”义律自辩在为“一场正义的、必需的战争”而战斗,又强调:“不要忘记,导致这场战争的中国当局的行为……是由英国臣民方面的严重错误造成的。”因为观念、职位、诉求的冲突,义律的言行举止相当矛盾,与中国人对他的一贯印象相去甚远。类似的认知差异,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源远流长。
南方周末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中国抱有仰慕之情,但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普遍的反华情绪,主要原因是什么?
蓝诗玲: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失败以后,参加这个使团的人对中国的判断,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写过对中国不大宽容的游记或者报告、汇报。巴罗的例子很典型。他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轻视,甚至可以说蔑视。这些作品出版后,对英国有比较大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写过一句话,意思是:英国人是用文字、用笔把中国消灭了。
说中英矛盾的根源是经济、贸易,是因为清朝不愿意答应英国对两国贸易的那些要求,导致马戛尔尼等人说了那么多对中国不满意的话。
何伟亚有些观点值得注意。简单说,英国人没有资格谴责清政府不愿意答应他们的要求。那时候的英国人觉得,他们所谓自由贸易或经济有普遍性。说实在话,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系统。清朝有什么理由要服从这个系统,跟着英国人做事?
我很认同,每个国家都有主权,要控制自己的经济、贸易。如果清朝人跑到英国,向他们提一些要求,英国政府可能也不会答应。
南方周末 :这些变化,其实反映了英国或欧洲自己的变化?
蓝诗玲:是的。下学期我要开一门课,讲中西关系或中西交流的历史,大约从1600年讲到当代。这门课的一个基本角度,是西方怎么看中国。西方人对中国的观点,常常不说明中国内部的什么问题,而更能说明西方人有什么样的心情、心理状态。
南方周末 :英国讲贸易,清朝维持自己的朝贡体系,是否可以说,这种两国的不同理解,是战争爆发的原因?
蓝诗玲:当然。英国主张的国际系统和清朝所主张的对外系统,都觉得自己有普遍性。那时候的英国人看待中国有局限性,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愿意从清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比如,清朝不愿意让外国人学中文,进入广州城,或者在更多地方居住。英国人把这看做地地道道的排外,看做清朝非常骄傲的反应。但清朝不一定这么看,这是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
清朝并不排外。为了保护、增强自己的权力,他们吸收了欧洲很多不同国家的因素和影响,可以说比较务实。他们不是汉族人,但吸收了孔孟之道,还有蒙古、西藏的因素。康熙皇帝让传教士做制造武器、绘制地图等非常有用的事情。
南方周末 :你在书中讲到,当时英国在印度、阿富汗面临很多外部问题要处理,那这场战争是不是存在一些偶然性,本来可以避免呢?
蓝诗玲:战争里有很多复杂、暧昧的因素,不过我一再强调,基本根源一清二楚,就是贸易、经济、鸦片。英国政府不愿意放弃从鸦片里得到的利润和金钱,一定要趁机把鸦片合法化。这是他们比较重要的目标。
英国人让印度人种鸦片,鸦片处理后可以送到中国去,在中国用卖鸦片的钱买茶叶。茶叶送到伦敦,在私人购买之前,英国政府要收取关税。用关税做什么呢?很大部分用来发展英国的海军,没有海军当然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鸦片贸易与大英帝国的权力和存在,有太密切的关系。
到1839、1840年,英国议会、政治家还在考虑要不要调兵去中国。有人提出:算了吧,不做鸦片贸易,我们应该另找收入控制印度——卖鸦片的钱,有一部分用来保护英国在印度的政府。但是他失败了,大多数声音还是觉得,没法放弃用鸦片挣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有必然性的,里面有太多国家利益。
对英国人来讲,这是国耻,是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南方周末 :谁起了“鸦片战争”这个名字?
蓝诗玲:第一次创造和使用这个名字的,是一个英国记者,应该是1840年或1841年。这个名字,是为了讽刺英国政府的不道德行为。
南方周末 :为什么《南京条约》没涉及鸦片,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有所涉及?
蓝诗玲:根据英文资料,《南京条约》未涉及鸦片,主要因为当时中国官员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把鸦片合法化。主要是这个原因。
南方周末 :为什么两国在1909年达成禁止鸦片的协议?
蓝诗玲:一方面是清末的反鸦片运动;此外,大概在1870年代开始,英国有个非常活跃的反对鸦片的运动,差不多在同一时代,英国国内的鸦片也被禁止了。
2 渐忘鸦片战争,要么是故意要么是懒惰
语言一直给鸦片战争的研究带来麻烦。或接触有限,或囿于英语水平,中国学者对鸦片战争的英文资料掌握不多。而196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中能兼顾中英文资料,以分析鸦片战争脉络和细节的学者也不多。
近四十多年,英语世界的学者研究鸦片战争,主要依靠议会和英国外交部的文件、出征中国者的回忆录,以及传教士的书信等。“如果没人把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他们自己很少去中国搜集资料。”参加讲座时,蓝诗玲对读者们说,“在这方面,我也许可以做点工作,让更多英国人关心当时到现在这一百七十多年,中国人怎么看这场战争。”
南方周末 :讨论鸦片战争,英国人有没有更多地论及道德问题?
蓝诗玲:有。打不打仗,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少人觉得,英国不该打鸦片战争。很多英国人对于这件事非常反感,不愿接受。也许可以说,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很多英国人心中对鸦片战争深感内疚。内疚有时让一个人想道歉,有时也让人自我辩护。当时,他们不说这是“鸦片战争”,而说是“中英战争”。很多生意人或政府官员为这场战争辩护,是想让中国人开眼界……
他们把这种贸易看做一种极端的自由,自由、文明等很多东西就混在一起,当然很虚伪。
南方周末 :这场战争最根本的特征是鸦片,但英国人讨论时用的是文明、自由贸易等字眼,这其实是一种话语策略?
蓝诗玲:完全是。书里一个比较基本的观点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西方观察者看中国的时候,陆陆续续地吸收了这样的策略,内心非常矛盾。一些英国观察者提出,是中国使他们去打仗。我觉得,他们创造出了一个“中国”。何伟亚较早的一本书,《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提到,这个过程从18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不仅仅是鸦片战争才开始。
南方周末 :1845年,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为什么会展出林则徐的蜡像?
蓝诗玲: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表达因打败中国而产生的骄傲和自豪。在英国人原来的想象中,林则徐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很有威权的人。他们觉得,1842年把中国打败了,把林则徐的蜡像放到伦敦,可以表现出林则徐并没那么可怕。
南方周末 :为什么后来英国人对鸦片战争的记忆那么模糊?
蓝诗玲:要么是故意地要把它忘掉,要么是一种懒惰。这不是最近几十年的一种遗忘。为了了解英国人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我调研过英国的历史教科书,最早是19世纪末的。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有很多老教科书,直到19世纪末,这些英文教科书都会承认鸦片战争,有时候放在引号里面,或者会说“中英战争”。一般来讲是在谈香港的时候,因为教科书要介绍英国为什么有这块殖民地。教科书向学生介绍,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占据了香港。
但是,20世纪初,我看过的教科书突然开始说,英国“得到”了香港,莫名其妙。当然,最近几十年出版的英文教科书会很坦率地谈鸦片战争。不过我想请读者注意,20世纪初,英国国内有一种“把鸦片战争忘掉”的趋向。
我也在中国研究了一些从晚清到民国,甚至1949年以后的教科书。我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档案馆以及北师大的图书馆,它们有很多很老的教科书。我同时从中国的角度去了解,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了解有什么样的演变。
南方周末 :英国教科书的说法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蓝诗玲:写这些教科书的人已经不在了,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可以把这看做遗忘的开端。20世纪初,很多英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蔑视中国,或怀疑中国要侵略全世界。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来自鸦片战争的内疚感。他们非常害怕中国要侵略西方,出现了“黄祸论”。很多西方观察者知道英国在中国做过坏事,担心中国以后向英国报仇。
由于“黄祸论”,中国人移民到英国、美国和法国,要面对太过残酷的种族主义。想了解这种气氛,可以看老舍在1920年代写的《二马》。老舍还可以写得更极端一些。对于在英国的中国人,那个时候确实很残酷、很困难。
南方周末 :华裔学者黄宇和认为你“若隐若晦地高呼中国该打”,你注意到这种批评了吗?
蓝诗玲:没有注意到。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应该是黄教授对我个人观点的一种误会。我在书里和这次采访多次提到,英国之所以打鸦片战争,是因为要追求和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权利。我做历史学家,没法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辩护。面对这种威胁,清朝要自我保护,要反抗大英帝国的扩张野心是完全合理的。
鸦片战争是很可能引起争议的主题。我每次出书,没法做到权威,但要按个人能力尽量去了解。写作一本书,你才真正开始处理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理解。虽然不可能完美,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进步。我想尽量做到的,是不要把这场战争写得太情绪化。虽然冷静很困难,但历史学家应该尽量客观。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能不能看大量第一手资料,然后把意思反馈或表达给读者们,让读者自己去处理内部的矛盾。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是受害者。这场战争的后果太严重了,必须尽量了解战争的意义或脉络。
[来源]南方周末
